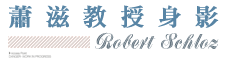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莫札特安魂曲莊嚴肅穆的樂聲,像一股生命的暖流,穿過國際學舍板椅上千百位聽眾的心房。台上師大音樂系合唱團和省交響樂團團員們,正聚精會神地投注在一位六+出頭的外國指揮身上。他,神采奕奕,雙眼閃耀著聖樂的光輝,通過他的指揮棒,將台上、台下的每個人帶入了莫札特崇高聖潔的音樂世界裡,而這座原本簡陋的籃球體育館,頓時間竟變成了一座宏偉的歌樂殿堂。那是一九六四年,五月初的一個夜晚的一場音樂會,這場音樂會為台灣樂壇締造了一次令人難忘的事蹟,並且也開啟千百個青年學子探尋聖樂的心扉,而這位當時引導著大家暢遊莫札特音樂神宮的指揮家,正是今天我們所敬仰與追思的蕭滋老師。
第一次見到蕭滋老師,是我就讀音樂系二年級那一年,當時的系主任戴粹倫教授在合唱課中,把他介紹給我們全系同學,隨即把這個課程交給他。起初,大部份同學聽不懂蕭滋老師那種帶有奧國口音的英文。以致於上課時,需要外文較好的高年級生替我們翻譯,但是由於蕭老師的學養和教學風範,上合唱課,竟成為我每週所最期待與神往的課程。
除了在師大之外,蕭滋老師也在國立藝專任教,並且指導台灣省交響樂團,他來回奔波卻毫無半點倦容。每次他一走上講台,就馬上全神投入,而整個教室也就充滿了學術的莊嚴氣氛。但是說也奇怪,那或許是音樂的力量,時間在蕭老師的形象與容貌上,從我第一次見到他起就定影下來,一直到他生命旅程的最後幾年,都沒改變,歲月似乎只從他臉上拂過,不留絲毫痕跡,有如竹影掃階,即使微塵亦不為之推移,然而,生命終究有其自然的法則,近十餘年來,病魔已逐漸侵蝕蕭老師的健康,但令人驚奇的是,蕭老師依然故我,和顏悅色地面對著真實的生命。每次我與家人去探望他,吳老師總會親切地把我們帶到他的床榻邊,而一看到蕭老師,迎面而來的,還是第一次留給我的那個令人難忘的容貌。宛如一幀永恆的畫像,嚴肅與慈祥的神態,在蕭老師的臉上,始終都是那麼地調和。
在大學裡上蕭老師的合唱課,我很榮幸地被他指定和高年級的張清郎同學,一齊準備莫札特安魂曲的男低音獨唱部分。蕭老師在課餘還撥出另外的時聞來指導我們幾個獨唱者,當時他還住在永康街巷道的一個幽靜小平房裡,有位通曉英文的男士為他處理事務,我們步入他的客廳,圍在蕭老師和他的那架老史坦威鋼琴旁作重唱練習。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氛,就好像在革瑞歐城堡的聖杯武士舉行讚頌儀式一般。記得有一次,蕭老師站起身來,用右手指揮我們歌唱,他因為全神貫注,以致於當我們唱到「垂念曲」的時候,他的長褲險些兒滑落下來,但他老先生卻面不改色,只用左手抓住自己的褲腰,而那段「垂念曲」很長,蕭老師依然指揮到曲子終了,才進房裡去加掛吊帶,當時我們目睹此景,居然沒有人敢笑出來,對於二十出頭的學生而言,能夠如此堅忍.誠然不易,而由此我們也可看得出蕭老師在教學時,是何等莊重嚴謹了。
師大畢業之後,我繼續跟隨蕭老師學習德文藝術歌曲,第一堂我準備了半場音樂會的德文歌曲去上課,但我們花大部分的時間在吟朗歌詞的詩句,品賞它的語韻和意境,然後探討作曲家被詩詞所激發出來的樂想。他告訴我說,我應該感激我的老師(戴序倫教授)為我打下的穩定與健康的聲樂基礎,蕭老師很客氣地說,他所能作的,只有在文化的層次上再作進-步的推敲和探討而已。因此他為我排定了曲目,從舒伯特、修曼、布拉姆斯、沃爾夫、到史特勞斯和馬勒,一系列下來,選擇代表性的作品來演唱,而由於蕭老師精闢的詮釋和指導,我每次上課就有一次的豐收。
我和蕭滋老師上聲樂課,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七年我服役海軍時為止,這期間我對蕭老師有了更深的認識。有一次,我們唱著修曼的埃森朵夫詩集,蕭老師說這是典型的浪漫詩歌,而當我唱到「月夜」的最後一句:
森林在夜裡低聲輕唱,星光一片燦爛
我展開心靈的翅膀,飛越那寧靜的大地
飛向我的故鄉。
顯然地,詩詞和修曼的音樂,觸發著蕭老師內心的某些想望,他頗為之動容。我也第一次發現,這位遠渡重洋,來此嘉惠我國學子的大音樂家,竟也懷有那麼深的鄉愁。後來,蕭滋老師和吳漪曼老師在親友和學生們的祝福下,結為連理,傳為樂壇佳話,蕭老師從此也就以此為家,他全心奉獻於教育。培育音樂界的後起一代,而事實上,在蕭老師的日常行儀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方藝術家與中國儒家師道的風範,他甚至在生前就已希望,他雖為一位西方的樂人,但要以他的這個第二故鄉,作為他日後埋骨的地方。
蕭老師除了豐富的學養之外,也十分關懷他的學生,但他卻是不輕易溢之於言表。最令我難忘的一件事,是當我回國,陷入在生活重壓的時候,蕭老師正與我在文化學院一齊籌劃歌劇「費加洛婚禮」的演出,與他老人家工作是一大安慰,總會使我暫時忘卻現實的煩惱。後來我突然收到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一張一萬八千元的支票,原來蕭老師觀察入微!看得出我在現實生活中掙扎,才私下寫信給張創辦人,最後我終於從吳老師那邊看到那封信的底稿,蕭老師寫著:「曾先生在華岡僅僅兼職,但為這次歌劇演出,他擔任導演,翻譯中文唱詞,並且親自演唱伯爵一角,奉獻出很多心力與時間,我請求創辦人,額外付給他一萬八千元。」蕭老師文辭簡潔,不卑不亢,而張其昀先生以其書生文人的本質,立刻瞭解情形而允其所請。蕭老師體諒一個人,竟有至於此者,現在我回想起來,依然感動如初。
在往後的幾年,我經常在蕭老師的指揮下,擔任演唱,對蕭老師豐富的學識,感受尤深。實際上,蕭老師對於歐洲傳統文化的修養,從思想到實踐,均堪稱一代碩果,尤其是德奧傳統音樂,蕭老師事實上就是這支文化命脈的表徵。去年我為文建會製作的音樂創作發表會中,曾以蕭滋老師青年時期的一首雙鋼琴曲--前奏詠、小賦格與展技曲作為整個音樂會的開始,在這首作品之中,我們即不難感受到巴哈的莊嚴。以及自莫札特,貝多芬等人直至布魯克納一脈相承的典範。在一九八五年,師大音樂系決定委請東和基金會出版這首曲子時,我曾跟蕭老師說:「您是位音樂教育家和演奏家,而您也有心作曲,精神令人敬服。」蕭老師則謙稱自己並非作曲家,但他接著嚴肅地說:「我作曲,旨在砥礪自己演奏、指揮和教學的能力,這就如同一個作曲者兼具有演奏能力,有助於自我創作一樣的意義。」這是一句至理名言,蕭老師的真知灼見,真令人讚佩。
由於教學與音樂會及歌劇演出的需要,我跟隨蕭滋老師學習指揮,他老人家對於指導作曲與指揮,遠比他教鋼琴課來得更有興緻,他常會超過時間,我上完他的一堂課,經常接連的就品嘗他一次豐盛的烹調(蕭老師對自己在廚房裡的手藝,跟他在音樂上的表現,一樣地顯得十分的自信)。當他執起指揮棒,那種專注的眼神和大師的姿態,即使在斗室之中,你的眼前亦能呈現出一個蓄勢待發的龐大樂團,在總譜上,他必記有明確的弓法,嚴格的樂句,和深究作品樂想的表情記號。他教導指揮,必由研究作品開始,非窮研作曲者之精神不予出發。在技術上,除了一般教授強調的點線之外,蕭老師甚注重樂句力度的延續與消長,尤其緩板的點線之間,力度的支撐,不允許有任何破綻,而這些技法,蕭老師說,乃在作為詮釋音樂的一種工具之學而已,一個好的指揮,最後所表現的,是他在知性與感性上的完美結合,包括他的學養和人格,以及他的情操,人生觀和精神思想取向。蕭老師教導指揮,先由巴哈的聖詠開始,再進入器樂,按年代的代表作,依序進行,甚有計劃,有時我遇到教學上的困難或實際的演出需要,也臨時作為特別的課題。我個人曾與楊波柏博士學指揮,並且也參加過義大利名指揮家費拉拉的暑期指揮研習營,但以得自蕭老師的受益最大。後來蕭老師把巴哈的合唱聖詠以及歌劇劇本十數卷全送給了我,他說:「你仍在學校教書,這些資料留在你那邊有更多的用處。」那本樂譜,尤其是那些歌劇劇本,都已泛黃,二次大戰期間的紙張質料不很好,書皮有些已經脫落,但對我而言,則如獲至寶,老師的贈書有著深遠的意義,是一種鼓舞,也是種期望。而那些絕版的歌劇書籍版本,正也是我從事歌劇研究所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一九七七年,我從維也納回來之後,為了逃避台北市的喧囂,很幸運地在陽明山向台銀租到一棟老舊的平房木屋,屋齡已近三十年,租金因此也不高,但我喜歡屋子前後那寬敞的草坪,還有窗外的蒼松和上千株的杜鵑,尤其更難得的是開門見山:那紗帽、大屯和七星山,就遠近地一線陳列在眼前。冬天我們還可在附近揀些香柏、馬尾松和相思樹枝,和好友們一齊燃起壁爐來談心,早晨根本不需要鬧鐘,因為房子四周的鳥聲會把人叫醒,白天偶而也會有蜥蜴爬進屋子裡來,它從脊椎起拖著長長的尾巴,油滑滑的綠得發亮。為了要點綴這一片的叢綠,同時也愛慕自然的芬芳,我在門前栽了五種不同品種的茶花,還有扶桑、七里香、櫻花和月桂,而季節一到,階前就是一地的蒲公英。我多次地邀蕭滋老師和吳老師上山一遊,最好是留宿一夜,享受一次假日的寧靜,但也許兩位老師客氣,他們都只到半途,就在圓山飯店宿夜,第二天清晨,反而邀我和內人下山去共進早餐。最後終於有一次,蕭老師和吳老師被我們請了上來,蕭老師立刻被四周的風景和新鮮的空氣吸引住了,他是那麼地喜愛大自然。當吳老師和我們在客廳上閒談時,獨不見蕭老師蹤影,後來我在後院找到他,他老人家把雙手背在後面,舒暢地走在草地上,就像一隻在池邊昂頭闊步的天鵝。
最近幾年,蕭滋老師的思想顯然進入了一個常人所難以探尋的精神領域,他從音樂推論出來的數理關係,演繹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有一次我到床榻邊看他,他以筆紙把他的理論演算給我看,但對一般人而言,要一時窺其思想的堂奧,何其容易?他曾指著櫃子上的一顆大蘋果說,它的存在是要根據幾個條件才能成立的,我當時雖不諳其思維方式,但是音樂、數理與哲學終極為一體的觀念,卻已從蕭滋老師的言談中得到證實,這也令人想像到貝多芬在極度的寧靜中,為詮釋其音樂與哲學的理念,而創作其後期絃樂四重奏的精神境界了。
蕭滋老師生於一九O二年,一生之中,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在困苦的年代裡,他深深地體驗到自我砥礪琢磨的艱辛歷程,因此愈發珍愛藝術。蕭老師與他同時代的一些偉大藝術家一樣,較具生命的毅力。而且富於同情心,對於人性的美德和道德情操,有著更深的執著。蕭老師這種氣質和心靈是很容易觀察得到的,因為他在這方面不僅溢於言表,而且力求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我課暇經常和他坐在桌邊閒談,雖然每次為時不長,但已足夠使人感受到蕭老師對於整個人類福祉的深切關懷。
提到蕭老師桌邊的談話,他可不像一些人那般的口若懸河,他常會思索一種結構簡潔,而且十分貼切與圓熟的句子來表達,因此他的句子與句子之間,常有靜默的片刻,這種無聲的境界,宛如中國繪畫中的「留白」,足可讓交談者對方在思維上有著游刃的空間與餘地。而在這時,蕭老師會習慣地以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不停地相互旋轉,速度十分均勻。好幾次我想告訴他,他那兩指間的旋轉,常會使我聯想起西藏喇嘛手上那永無休止的法輪,因為不管是蕭老師的手指頭,或是喇嘛手上的法輪,只要將它無限度地放大,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宇宙運作的形象了。
但是,我始終未向蕭老師提及我的想法,或許他會笑我何以將信奉天主的他,用彿門聖事來作比擬。其實我想也無妨,萬物本屬同源,只因為人類生命苦短,而在有限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中,對神的認知有限,因此而有了差異。我們常聽說:上帝根據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我也不免懷疑大概是人根據自己的造型去想像了上帝。因為我們把上帝給「擬人化」了之後,就可以在心裡塑造一個栩栩如生的偶像,這樣一來,十分方便於向他禱告和祈求。基督教的教義是十分肯定,不容置疑的,其全能至高的神都有了名字,而且除他之外別無救贖,換句話說,答案已為你揭曉,問題只在於你信與不信之間;而佛教則不然,佛本身只指示你通往淨土的路途,他強調悟道的過程,使你無法一蹴可及,你必須萬德具備、洗淨塵世煩惱,俟無明已盡,方能進入大覺的至高境界裡與神同在,是為涅槃.然而芸芸眾生,造化隨緣,並非人人都得立地成彿。蕭滋老師與我在人文宗教信仰上顯有不同,但既知萬物同源,因此現世不同的宗教觀應能殊途同歸,至少目前可確定的是:他與我對大自然的賜與同懷感激;對晝夜的更替,四季的循環和宇宙的秩序一樣驚喜;而對於主宰著這一切的至高至大的精神力量同感敬畏,並且獻與最虔誠的讚禮。因此在形式上與名義上的差異也就無損於最終的弘旨了。這就如同生長於不同地方的蓮花,而被賦予不同的名字,但它一樣是蓮花,它根據相同的自然法則,怡然地滋長綻放,不同的名字,並無損於它本身自我圓滿的生命意義。
蕭滋老師是走了,他去到了一個不可知的另一個世界,吳漪曼老師告訴我們蕭老師臨終前的情景:安祥、和諧,並且聽到唱得很美的花腔女高音,彷彿蕭老師望見天使撲翅,仙樂飄揚,我想也唯有一顆高貴的心靈,懷抱著堅貞的信仰,才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仰望到另一個世界的美景,這種死亡的境界很高,非人人可及。而在現世裡的想像中,我們望不見冥河的擺渡,我們只知道,蕭老師伴著他人間天使般的吳老師的聲聲呼喚,已逐漸遠去!匯入永恆。
莫札特安魂曲莊嚴肅穆的樂聲,像一股生命的暖流,再度穿過席上千百位人們的心房,這回是在聖家堂為蕭滋老師舉行的安魂彌撒,我手握著指揮棒,面對著師大音樂系,台北歌劇合唱團,和遠自台中而來的曉明女中管絃樂團的學生們,百感交集。回想第一次蕭老師指揮我們唱這首安魂曲時,眼前這群青年學子,才剛剛出世,有的還未誕生。而就在去年的蕭滋老師慶生音樂會中,我曾帶著這個歌劇合唱團,演唱了莫札特的兩首宗教曲子。後來蕭老師聽了錄音帶,在電話中告訴我說他很喜歡這個合唱團,成員不多,但很精緻,他打趣地說,希望他過世的時候‧這個合唱團能為他演唱巴哈g小調的一首聖詠,我笑著回答說,那就讓我們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吧,蕭老師很幽默的補了一句:「你們得快準備,否則可要來不及呢。」而今一年剛過,我卻沒有以巴哈的那首聖詠來紀念他,我相信蕭老師該不致於責怪我未實踐諾言,只因我認為在他追思的大禮彌撒中,領著這群莘莘學子,演唱這首師從於他的安魂曲,更有意義:這是蕭老師臨別時所給與我們大家的再一次教育,至少學生們暸解了安魂曲的章節,在真正的追思彌撒中是怎樣地實際安排。在我的記憶裡,這應是國內首次的大禮彌撒,就像二十三年前,蕭滋老師首次介紹給國內,演唱這首震古鑠今的安魂曲一樣地值得紀念。我知道蕭滋老師是詮釋莫札特作品的權威,但是當天我在他靈前指揮這首安魂曲,卻絲毫沒有班門弄斧的感覺,我只感覺蕭老師好像就站在我的背後,要求著他所希望的速度和力度,包括第七首的「流淚之日」中,第一小提琴和女高音聲部的一個八分一音符應稍作停留。而另一方面,站在我眼前的又是一群年輕的學生。我似乎是身處於兩代的夾縫之間,牽引著-條注滿了希望的繫帶,深怕它會有所斷裂,而隨著時光巨輪的推移,也愈發令人感於薪火相傳的莊嚴意義了。
安魂彌撒甫畢,我放下指揮棒,仍坐於聖家堂的樓上,我轉身俯視蕭滋老師的靈柩,在親友的注目禮和六位音樂科系主任的扶持下,緩緩引出教堂,在這短暫的時刻中,我努力地想將認識蕭老師以來二十餘年的光景,快速地在腦際裡重新掃描一次,但是往事太多,思路一再擱淺,尤其回憶到第一次在他住所練習這部安魂曲中第五首「垂念曲」的情況時,他那一手抓住腰帶,一手努力指揮我們歌唱的神態,又親切地浮現在我眼前,那情景就好像是-首莫札特詼諧的「嬉戲曲」,因此我不禁泛起會心的微笑,雖然此刻大家的眼眶都已潮濕。
我們一行,跟著車隊送蕭滋老師到了三峽的墓地,這是吳漪曼老師特別為他卜選的埋骨地方,環境十分優雅純樸,我抬頭看到對面,不免暗暗驚奇,因為青翠的山巒十分俊秀,恰似薩爾玆堡河邊山嶺的造型,不知道這是吳漪曼老師對輿圖細心的選擇,或是冥冥之中的巧合。但是事實上這已不是重要,蕭滋老師後半生全貢獻給中國的音樂教育,台灣已是他的另一個故鄉,如今他已可神志飛揚,再無形體的負擔,只要他心之所往,千里往返,瞬間可及。我們在此追思他,只因為他的愛心與藝術的信誠,溫暖了無數學子的心房;我們在此感念他,因為他為後代的音樂家們,樹立了一個完美的精神風範。因此,安息吧,蕭老師!青山已收你骸骨,你將去到另一個世界,在那世界裡,不知道是否也有蓮花,如果有,請也不必在意它叫什麼名字。我們在此只希望你的靈魂永遠的安息,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