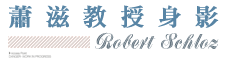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前言
記得那是一月十二日晚上大約九點半所發生的事了。
電話另一端傳來和藹可親的吳漪曼老師甜美悅耳的聲音。她希望我能為蕭滋教授之百歲冥誕寫一篇字數不拘的文章,敘述在一九六○年代他與我之師生關係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她是這樣對我說的:「吳老師,我有個請求,……可以不可以呢?」。她是那麼的客氣、那麼的誠懇,身為學生的我,怎不深深感到受寵若驚呢?為了要即刻行動,我就把當時手邊的工作暫擱下來,盡力試著回想逝去已久的那段年代。但是,對早已「轉換跑道」、被同學稱為「音樂系之叛徒」的我來說,要穿梭於迥然不同的時空裡去找回那遙遠的過去,談何容易?想著想著,我頓時陷入時光的隧道中,久久無法自拔‧‧‧‧。
交會頻繁的一年
三十九年前(即1963年)的夏天,從美國彼岸來了一位「音樂天使」,在我們美麗的寶島這片園地中,奇蹟般找到了他「最多的愛」,二十多年如一日,不遺餘力地終其一生在這兒播種、培育、灌溉、乃至收成。他就是我在台灣師大唸音樂系那個時候的鋼琴老師一和藹可親的蕭滋教授。
我們首次交會的地點是當時的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USIS)。我那時還是個大三學生,只因先前贏得全校盃英語演講比賽之冠軍而被系上派去當蕭滋教授在那兒所舉辦的鋼琴講座的口譯員。他當時指導的小朋友有好幾位,男生女生都有,其中依稀記得有一對可愛的姊妹花叫秦慰慈似的(註一)。蕭滋教授來華之前雖曾定居美國多年,但其「鄉音」還是「無改」。一般人要聽得懂他那帶有非常濃厚的奧式德語腔調的英語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兒喔!開始幾次的口譯我都是緊張得如坐針氈、坐立不安,深怕無法扮好自己的角色而對不起蕭滋教授。還好,後來逐漸就適應了。我那份差事雖說壓力頗大,但卻羨煞系上同學。為什麼呢?一來,我可以站在「最前線」聆聽資優兒童們精湛的演奏;再來,還可以用「特寫」的方式觀賞蕭滋教授的指法、表情和風釆,以及領受大師鉅細靡遺之獨特教法。
其實,在大二開始修讀義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等外語後,自覺在外語學習的領域中樣樣得心應手,如魚得水那麼快活。從此心裡深處漸漸產生了無法抗拒的渴望一那就是大學畢業後非得朝向語文研究這個方向謀求發展不可,否則就可能會遺憾終身!面對資優孩童們高人一等之表現和蕭滋教授爐火純青之琴藝與廣博精深之涵養,相形之下,我是那麼的心有餘而力不足、那麼的微不足道!在這般猛烈無情的衝擊之下,打從心底裡就萌生了「背叛音樂」的念頭了!
升大四時(1963-1964),系上共同必修課「合唱」由蕭滋教授擔任指導。我順理成章又被派負責口譯,是故每週都有與蕭滋教授定期的交會機會,「近水樓臺先得月」式領受老師與眾不同的指揮法。有了在美新處之口譯經驗,對自己在合唱班的表現因而較有信心,起碼不像以前那麼緊張兮兮就是。雖然如此,我始終還是聚精會神聆聽老師之講解,絲毫不敢掉以輕心以免出洋相。事實上,有幸上他的合唱課,的確是一種享受:他臉部表情很細膩、很豐富,音感異常敏銳,我有時覺得連他的指揮棒都好像會說話呢!他對不同樂句之分段、連結、以及速度、音量等方面之變化,要求極其嚴格:稍有偏差,就不厭其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練習直至完美無缺為止。對諸如adagio/lento和piano/pianissimo有其獨特的處理法(註二),害得同學們有時都喘不過氣來,有時連自己的呼吸都聽得到呢!
那個時候許多音樂會都在中山堂或國際學舍兩處舉辦。蕭滋老師所指揮的,不管是交響樂、室內樂或合唱,對國內愛樂者而言,場場都是難能可貴的音樂洗禮,而對我們這些音樂科系的眾多學生來說,每場演出均為回味無窮之音樂饗宴、取之不盡之學習素材。記得凡是在"Messiah"或"die
Jahreszeiten"(四季)等大型合唱曲擔任獨唱的同學,他們合唱課的分數系上規定要加分,這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我呢,擔任全年的口譯,沒有功勞,亦有苦勞,卻連半分都不加,這樣公平嗎?針對這樣的差別待遇,當時有無向打分的助教李智惠老師反映,不得而知了;不過,只記得不敢向蕭滋老師訴苦就是。
當時系上規定每一年級推派一位主修鋼琴的學生跟蕭滋老師學琴。不知為何,我被選為畢業班的代表,因此我們師生間之交會就更頻繁了。我猜想,我之所以被選上,主要是借重我的經驗幫學弟妹們做口譯,因為班上琴藝佼佼者有的是,絕不會輸到我這個乏善可陳、起步已晚的僑生吧!我先後師事林運玲(註三)、高慈美、周崇淑和吳漪曼等老師,從他們各有千秋之教法當中吸取了不少的寶貴心得。記得吳老師處學過Mendelssohn之"Jgerlied"
(Op.19,No. 1)和Handel之"The Harmonious
Blacksmith"(Air con variazioni),周老師那兒已彈過Brahms之"Rhapsody
Op. 79, No. 2"和Mozart之"Sonata
KV 331",所以程度雖不如人,但自覺技巧漸趨佳境。一直到了正式成為蕭滋老師的學生後,我才真正體會到鋼琴路途之艱辛與遙遠。
當其他同學正埋頭苦幹,準備畢業演奏的「大」曲子時,老師就是要我一切從基本學起。上學期大半時間是學習如何放鬆手指、手掌、前臂和上臂,如何利用手指各部位觸鍵,如何練成十指各自獨立且保有彈性,以及如何掌握以手指關節、手腕、手肘和肩膀為重點之彈奏法。每天練習時還得閉目揣摩各項技巧之異同所在。日復一日的苦練,終於發覺自己的技巧有了顯著的進步。又因廢寢忘食般的勤練(有時多至每日十小時),更而獲得「琴房游擊大王」之美名!種種苦盡甘來之感受曾令我一度重新收復失去已久之信心。當同學們一個接一個、問東問西地要我講解或示範蕭滋老師之指法與教法時,怎教我這個被笑稱為「蕭滋教授之代言人」不沾沾自喜,甚至偶爾得意忘形呢?
隨著畢業演奏之逼近,我赫然面臨一大危機:萬一老師不讓我上台,屆時我怎「下得了台」呢?事實證明我當時之憂慮是多餘的,因為他決定讓我練Chopin之"Polonaise
Op. 26, No. 1"作為我畢業演奏的曲子。這下我才鬆了一口氣,真是謝天謝地!幸好畢業演奏那天我沒出醜,不然就辜負了他老人家一整年為我「量身訂做」之教學法與苦心了。
聲樂方面的畢業考,戴序倫老師讓我唱的是Schubert之"der
Lindenbaum"(註四)。考前徵得蕭滋老師之同意就帶了伴奏葉君明同學到老師住處向他請教。他聽了之後,好像做了如下的評語:"It's
not a great voice, but…not bad."他這樣適時鼓勵學生,令我高興了好一陣子。他之所以有那樣的看法,我想應該歸功於我清晰的發音和咬字吧,因為那個時候我正如火如荼勤練德文(註五),同時亦已開始申請西德波昂大學入學以便師大一畢業就要「改行」,赴歐專研語言學去了。對於這項「背叛的秘密」,我一路守口如瓶,不敢讓老師知道就是。
後語
躬逢蕭滋老師今年十月十六日百歲冥誕,真想在此由衷向他老人家說聲「祝您生日快樂!」;可是,他聽得到嗎?
如今年逾耳順的我,還是很喜歡到兩廳院去欣賞各種音樂活動,心血來潮時亦會唱唱"der
Lindenbaum",但Chopin之"Polonaise"早已淡忘了。不知老師在天之靈會不會責怪我?
總之,我深信我們師生兩人還會有一次的交會,而且希望是發生在他故鄉Steyr那兒的交會,因為總有一天我會專程拜訪其位於Steyr和Enns兩河交匯處,靠近橋邊的Bahnhofstrasse,門牌為1-3號樓上之故居,並向這位自遠方來台的「音樂天使」致敬。只怕到時他老人家會悄悄地對我這個「音樂叛徒」說聲:"Wer
bist du?"(註六)
附註
註一:後經吳漪曼老師證實為如今已成名之秦慰慈、秦蓓慈姊妹、陳泰成等人。
註二:筆者就讀於倫敦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時曾考進LSO(倫敦交響樂團)之合唱團,當時的指揮為Georg
Solti。他的指揮法有些方面令筆者聯想到在師大時的蕭滋老師。
註三:為留澳之鋼琴家,是筆者之聲樂啟蒙老師申學庸教授所推介認識的。
註四:筆者留德期問曾在1965八月問赴Bayreuth參加Internationales
Jugend Festspieltreffen其中德國藝術歌曲與合唱等活動,並曾在波昂之Bonner
Opernstudio師事男高音W. Muller-Lohnsdorf專攻Schubert
Lieder - 1968年獲得倫大普通語言學與語音學之博士學位後,以歸國學人之身分回母校任教於英語系所至今。當時有幸被校方安排住在蕭滋老師以前在和平東路巷內充滿甜美回憶之居所,前後共兩年。這期問因時常感念蕭滋老師,曾數度有意向老師請益以便開一次Schubert
Lieder之獨唱會,只因始終鼓不起勇氣踏出第一步而一拖再拖。又因專注於外語教學,分身乏術且備受「隔行如隔山」、「一口不可兩用」之壓力,而後只好作罷。
註五:返國後曾在本校英語系、數學系和體育研究所教授德文。在張錦鴻主任任內曾應邀在音樂系教過德文一年。
註六:「你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