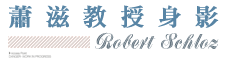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初次見到蕭滋老師是在當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室內開著低溫的冷氣,凍得我渾身直打哆嗦,而他老先生則滿臉紅光,頂著福態的身軀,顯得頗為怡然自得。因為寒冷的綠故,我先彈了一遍音階暖手,再彈舒伯特〈即興曲〉。雖然好像有得到外國老先生的讚許(他講的是外國語),但其實並不知道這樣彈到底算不算好,蓋因當時的環境並不容易聽到演出,僅只憑著直覺大約這麼個彈法。不知過了幾天,被通知可以去跟老先生上課,從此開始了我們的師徒關係,成了蕭滋老師來台最早期的學生;同樣地,在美國新聞處上課。
老先生先從手指訓練著手。光是單音、音階、琶音,就練了一、兩個月,果真觸鍵就紮實、明亮多了。接下來才是克拉曼、皮希那、徹爾尼、克萊曼悌;當然啦,巴哈創意曲、一般樂曲自不在話下。老先生對指法極為重視,每一首曲子都要親自彈過,仔細地寫上他的指法,有時,還要我試彈某些片段,以便找出最適合我手型的指法。因此,在當時極為貧瘠的音樂環境下,聽他彈琴就成為唯一的指引了。
另外,他還陪我彈四手聯彈。除此之外,在一週兩堂的琴課外,還安排了幾位前輩音樂家與我合奏室內樂。和聲學後來也是「必修課」,本來也曾打算要我學單簧管,不知何故作罷。至於演出方面,有時在耕莘文教院,但似乎不是目前這一棟。有一次比較大型的學生發表會是在國際學舍的籃球場─當時台北最重要的表演場所─舉行的。我十一歲與當時國內唯一的樂團─台灣省交響樂團彈協奏曲也是在那裡,由蕭滋老師擔任指揮;我們的室內樂組合還上了幾次當時唯一的電視台一台視(在當時當然都是現場演出直播),也曾到南部演出。我出國前在國軍文藝中心又彈了一次協奏曲,仍然由他擔綱指揮。
老先生的好友豪齊克教授有幾次路過台灣來拜訪他,我就會被找去「秀」幾首。至於聽我彈琴之後,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交談我就聽不懂了。另一位要我去「秀」的則是定居菲律賓的一位白人女士。只記得她一踏入客廳就滿室生香,瀰漫著濃郁、怡人的香水味。
我十二歲時應馬尼拉扶輪社邀請赴菲演出,其中包括一家女子中學。彈了一連串曲子後,受到熱烈的鼓掌,獻花時還遭女生親臉,我立刻滿臉通紅。到底當時國內還不流行握手,遑論擁抱、親臉了,受到這樣的「禮遇」還要感謝老師指導有方。
家居方面,蕭滋老師有一位王先生幫他打點家務事,包括買菜、烹飪。老先生似乎很在意飲食的口味,印象中他偏好牛肉,時常自己下廚露兩手。有時他會帶我們幾位學生到位於中山北路的美軍軍官俱樂部用餐。在當時只習慣吃炒肉絲的年代,能吃到整片牛排可是很稀罕的事了。我還記得老先生特別喜歡葡萄牙的玫瑰酒。
跟蕭滋老師習琴三年的種種,真的感激他栽培我成為鋼琴家的用心。老先生來台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行文至此,覺得自己彷彿已經成為歷史的見證人了。時代永遠在變遷,然而蕭滋老師以鋼琴家、教師、指揮家、作曲家身份,給台灣音樂界留下深刻的影響,也在台灣的音樂史上確立了他不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