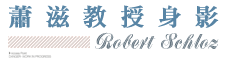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今年十月十六號是蕭滋老師一百年冥誕的日子,我提筆寫此文時,正值復活節前夕,這不禁令我憶起跟老師習琴那幾年,每逢復活節,老師必定請老王染了好多不同顏色的蛋,每個學生都會拿到一小籃用很精緻的竹籃子裝著的彩色蛋,還有一些包裝得五彩繽紛的巧克力。我那時對復活節根本沒什麼概念,但是上完課後,小心翼翼地捧著那一籃蛋,乘坐三輪車往火車站時,那種喜孜孜的感覺,我一生都不會志記。現在閉著眼睛,我還可以看到太陽的光線照在五顏六色的蛋上,呈現出橙、黃、藍、綠……等色彩,這一幅由光線與色彩交織成的畫面,在我腦海中持續不斷地擴張,蔓延‧‧‧‧,逐漸地編織成一段彩虹般的回憶─
一個蕭滋老師送給我的,屬於年少時期一段令人難忘的記憶。 我跟蕭滋老師學琴時,年紀還小,雖然知道老師是一位卓越的音樂家,有一肚子學問,且經驗非常豐富,但是他到底哪一點與眾不同,他的藝術與人格修養是在什麼樣的層次上,其實我那時是無法體會的。日後,等到我自己也為人師時,再次回頭觀看跟老師學琴的情形,方才了解,老師在教學上確實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且有步驟、方向與目標,以及豐富的美學修養與體驗,他的為人心胸寬大、視野深廣、樂於付出,且在藝術的領域中能夠不斷的深入探討、精益求精,研究範圍甚至延伸至其他的思考領域,永不停懈。
蕭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雖然已過世多年,但他在我們心目中建立起的一個藝術家的形象,以及他把自己融入音樂中,又讓音樂融入生活裡的存在方式,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境界。
我想先稍微提一下,當蕭滋老師踏上台灣這塊土地時,迎接他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景象。蕭滋老師於1963年來到台灣,當時台灣樂壇的狀況,若拿來和今日的情景相互比較,真有如幼稚園之於大學。六十年代的台灣,既沒有音樂班,也沒有任何從小培養音樂人才的制度,學音樂的小孩大部分是學鋼琴或小提琴,選擇木、銅管等其他樂器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全省能夠演奏的樂隊,大概就只有台灣省立交響樂團了。而那時候台灣的經濟狀況以及各項建設都還沒上軌道,藝術只是被當作奢侈品看待,並不能夠成為一般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
那幾年,偶爾會有美國國務院派來的演奏家或樂團來台演出。我記得有一年隨父親坐了七、八個小時的火車上台北,為的就是要聽美國茱麗亞弦樂四重奏在中山堂的演出,對於父親看到在觀眾席中,有人因為喝汽水而弄出一些瓶瓶罐罐的砰擊聲感到十分生氣(或說洩氣)的場景,記憶猶新。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回憶是,有一年鋼琴家豪濟克先生來台南演奏,當時台南並沒有正式的音樂廳,演奏會大都是租用學校的禮堂演出,當然,禮堂裡也沒有冷氣。豪濟克先生在台南演出時,正值盛暑,主辦單位別出心裁地在鋼琴旁邊放了一塊有半個人高的大冰塊,電風扇則由冰塊後面吹往演奏者,因為冰塊就放在以前家裡用來洗衣的大鋁盆上,或許是放置的重心不穩,當豪濟克先生彈到一半時,冰塊居然倒了下來,全場嘩然,豪濟克先生倒是毫不在意,還開懷的笑了一場,然後四平八穩的繼續他的彈奏。對於這一幕,至今,我還是不能忘懷。在這兒提到這兩件事,只是想讓年輕的讀者對那時台灣樂壇的狀況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蕭滋老師剛來台灣時,面對這塊土地、這兒的人以及台灣樂壇的狀況……等等,他個人的感受如何?他自己的心情又是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他那時已六十出頭,對一般人來說,差不多是已屆退休的年齡了,但是對一個像蕭滋老師這樣一位真正的藝術家而言,當他面對自己的工作時,是沒有所謂退休這個念頭的,因為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之源。
我常懷疑,在生命重要的轉捩點上,人是否真能看透上帝的旨意或命運的安排?當年的蕭滋老師,恐怕也無法預知他將會在台灣待多久,或將為台灣樂壇帶來一番什麼樣的情景,而憨憨學子如我們,當時對於那即將參與的台灣樂壇啟蒙之旅,也是毫無所知的,我們只是跟著老師所給的方向,走上了各自生命中的音樂旅途。
我今日回想蕭滋老師的教學,其實很多細節都已成了模糊的影像與拼湊的片段,若想要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教學法出來,似乎是不太可能之事,但是,他有一些方法與觀念確實讓我受用不盡。首先,我非常感謝他幫我在古典曲目上打的根基。在跟他學琴的那幾年裡,我從來未曾間斷過巴哈以及其他古典大師,如貝多芬或莫札特等人的作品練習。我對古典作品的形象,以及觸鍵、樂句、結構、美感經驗等,就是在那一段時問裡建立起來的,且於往後的日子裡,得以藉著音樂的媒介,進入古典美學的領域,實實在在體驗了藝術與人性結合、昇華的過程。
以我自己教學的經驗來說,如學生彈奏古典樂曲的根基不夠紮實的話,那他彈浪漫派或是其它樂派的曲目,就容易流於輕薄、膚淺,且在定型後要回過頭來學習古典曲目時,總是會碰到事倍功半的狀況。古典音樂(包括巴哈等作品詮釋)難就難在它的美學境界,以及它要求個人的內省、節制與沉澱。這需要長年的教化與薰陶,並且一定得給予那些有意願在這個領域上持續探討的人足夠的時間,讓藝術的表達與人格的內涵相互激盪,互持互長。經驗告訴我們,若要等到它在精神上開花結果,總是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或更清楚地說,它是終生的事業。
我很慶幸,在我智性正在萌芽之年,能認識蕭滋老師並且跟他學習,老師在音樂上的造詣,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而他本人給我們的感覺,就具備了自然、穩重、智慧、幽默與和藹可親的美感,一種和諧的美感,一種存在於古典美學中令我極為嚮往的美感。我想,如果當年碰到的是一位心態不平衡、暴躁易怒、情緒化又自大的老師,那我所感受到的「人與藝術整體性的美感經驗」又會如何?實在不敢想像。
蕭滋老師所給的曲目,從來不會超出學生們所能負荷的程度,而且大概是受了他自己品味的影響,他不會給一些次級的作品,也不會給一些太過炫技的作品。老師選的曲目,總是能讓我們以一種自然健康的方式,很踏實地去認識一些傑出的作品。老師當年排除萬難,讓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跟一些管弦樂的老師們合奏室內樂,並且還違反校規,讓藝專管弦樂團在校外和我們演出協奏曲。他還幫我們安排了理論方面的老師,讓我有幸跟著廖年賦老師學了幾年的樂理。現在回想起來,今日的音樂學子認為理所當然地在學校就可以學到的許多課程,當年都要靠蕭滋老師有計畫、有心的推動,才能彌補我們那個時代學習環境中的空白。
我跟蕭滋老師學琴時,因家住台南,只能隔週的週末乘坐火車北上,在姑母家過夜,隔天到老師家上課,上完鋼琴課後再到廖老師家上樂理,下課後即搭乘傍晚的火車或夜車回家。我會在車上昏暗搖晃的燈光下看書,準備隔天學校的考試。那時蕭滋老師給的作業,每次均包括四首不同時期的曲目,還有練習曲以及Pischna手指練習範本。老師每次一定仔細聽完所有的曲目,並且在樂句解析、音色拿捏、速度控制以及指法上,一一講解示範。
技術方面,老師特別注重手指放鬆而獨立的運作,以及正確且合乎音樂性的指法。我不記得在那段時間裡,我的彈奏有任何不好的姿勢或壞習慣,倒是後來在維也納學琴時,可能因為肢體放鬆沒做好及力量的運作不對,加上曲子越彈越重,身心不堪負荷,結果回國時,除了帶回一張特優的文憑外,也帶回一身緊繃的肌肉。回國後,我自己利用各方面所能得到的資訊,狠狠的在身體運作、力量操控、姿勢、放鬆、呼吸等各方面下了一番功夫。那時候只要接觸到一種新的演奏方法,我一定身體力行,就運用那種方法實地的去練習,幾十年來,不知練過多少種彈奏的方法,到頭來,我才發現,原來蕭滋老師最強調的手指獨立彈奏方法,才是最重要、且最基本的觸鍵法,其它所學,譬如:手腕、手肘、手臂等的運用,全部都需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當這個基礎不夠穩固時,就像房子的地基不夠堅牢般,蓋在上面的建築物,是既危險又不能持久的。
蕭滋老師的教學法中,還有一項與觸鍵、音色、身體的感覺直接有關的,便是他對指法的運用與重視。我到現在還保持著一種習慣,即是在練新曲子時,第一項工作便是決定要用什麼指法,必要的話(譬如說,要改變譜上的指法時),我會將它寫在樂譜上。我們都知道,印在樂譜上的指法並非是絕對或是唯一的選擇,但那卻是專家們仔細推敲、並且實驗過的一種。蕭滋老師跟他的哥哥海因茲,就曾一起出版過兩冊《莫札特鋼琴奏鳴曲》的版本,這個版本的特色就在於它裡面的指法,而這些指法,都是配合樂句的走向、起伏及性格等音樂性的考量而設計的,非常值得去參考與應用。我最近又再一次仔細的研究這個版本的指法,竟然發現許多以前沒注意到,但是卻十分令人拍案叫絕的設計,其中有許多樂句,確實沒有那樣的指法,就做不出理想中的音色與感覺。這是我為了寫本文而得到的意外收穫。
指法有它自己一套位置排列與運動走向的邏輯,好的指法會幫助你做出應有的音色,有時也會使樂句的性格格外突出、彈奏更加穩定,且在背譜上有極大的幫助─因為手指的運作會有一種慣性,這也就是演奏家不會在上台前幾天變更指法的原因。
蕭滋老師教我們習慣於運用好的、正確的、以及合乎音樂性的指法,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有意識」的運用指法,也就是說,當眼睛看到音符時,並不是由恰巧放在那個位子上的手指來彈下去,而是經過大腦的邏輯思考,配合全身一致性的感覺,才把音符彈奏出來的。這個習慣的養成,越早越好。我以前教過一個已經上國中的學生,那時曾經費了好幾年的功夫,都無法改掉他從小養成「無意識運用指法」的習慣,而後來這也成了阻礙他彈琴時更上一層的主要原因。
在這兒,我只能道出蕭滋老師教學內容之一二,且這內容,是屬於方法性的領域。至於在藝術性的層面上,一來因為藝術的內涵並不是靠邏輯或方法就可以解釋得清楚的,外加上我們那時候的程度跟老師相差甚遠,所能體會的有限,因此實在是難以描述。若以我現在的認知來回想當年的學習情況,我倒是覺得那時從老師那兒直覺感受到的,關於「一個藝術家的形象」,在往後的日子裡,一直持續在我體內醞釀,進而形成人格發展過程中的催化劑,也直接影響了我的教學心態與藝術涵養,這是我那時候的年齡無法料到或體會到的。
知一教一,或知十教一,其知識與氣度是有別的;從單一事件,或從歷史過程中論事論人,其眼光與智慧,是不同的;言語背後是否具備一顆真摯的心,或音符背後有否美學的支撐,其胸襟與境界也是不同的。一個老師交代一句話、一個音符、或一個觀點時,學生聽到的,可能就是這句話、這個音符、或這個觀點,但是,他所感受到的,卻是構成老師這個「人」的整個大背景
─ 他的學識、風格、觀念等,這兒雖然沒有孰重孰輕之分,然而,後者的無形影響,卻是更深、更長久的。
作為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我們總是期待最終能夠表達出「人與藝術結合」的成熟風格,而這個風格,應該是貫穿一個藝術家信念、格調、涵養、與技術的一種全方位表達。換句話說,風格的臻於成熟,就是架構於個人的美學觀點之建立上,它包含對己、對人、對神的信念,以及對美的事物、美的人性之嚮往。一個好的藝術家,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把人性與藝術做出完美結合的那一個人。
一個成熟藝術家的人格,應該是完整的,因為它沒有被虛偽、矯飾的情感分裂出去;藝術工作對他來說,代表的不只是職業而已,更是心之所嚮、情之所託;藝術透過它,得以滲透到眾人的心靈,而他,也藉著藝術得以找到靈魂的慰藉與精神上的自由。這是一個伊甸園的境界,身為一個老師,當他站在這樣一個高度時,他的學生自然會嗅到、感到一股靈氣,於是,一顆滲透進骨子裡而在潛意識裡萌芽成長的種子,也就在學生身上形成了。這,應該就是所謂的「教化」吧!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隨時隨地受到周遭的人─特別是我們的師長─影響的,這影響的面向有許多的層次,其中屬於方法性的教導,其實只能滲入皮骨而已,藝術性的薰陶,卻是可以箝入血肉裡的,至於人格的感召,則是跟著氣在身體裡運轉,是一不可言喻的全方位教化。
好的藝衛家,藉由品味掌控技術,並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逐漸確立風格。而風格的形成,最終又決定於人的性格、美學觀、與文化背景。我們在蕭滋老師身上看到的是一個人格與藝術合一的形象,以及一個教育家的風範。今日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濟與科技掛帥,又是消費導向的時代裡,人們的生活表面上看起來熱鬧忙碌,骨子裡,人性卻又時常迷失到幾近荒唐的地步。有時,當我自己也感到迷惑時,我會回頭看看老師走過的道路,他給的一個具指標性的方向,以及他對人性的最終信念,於是,我的心又再次地覺得踏實了。
像蕭滋老師這樣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能夠在六○年代來到台灣,且持續地在這塊土地上耕耘了二十多年,實在是台灣樂壇的福氣,我們這一群當年從他那兒得到知識與教化的學生,如今也都各自站到教育的崗位上,為下一代貢獻一份心力。在世代交替的文化傳承中,藝術之陶冶人性,是既緩慢又迂迴的過程,但我們仍希望,將蕭滋老師交過來的棒子,順利地移交給下一代,這個過程應該不只是單純知識的傳授,而是涵蓋生命經驗的「悟道」之啟發,我們追求的境界,是一個人與藝術、與生活融合為一體的伊甸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