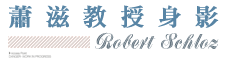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二○○二年四月返台開畫展,巧遇蕭滋博士的夫人吳漪曼教授於東之畫廊,言談中吳老師囑意為蕭滋老師(Scholz
1902-1986)百年誕辰為文一篇,並盼望多著墨蕭滋老師與國立藝專管弦樂團的其人、其事、其藝等互動紀事。當場隨即答應吳老師努力追憶,並將時光倒回一九六三年的初夏,當時我還是國立藝專音樂科一年級的新生,主修小提琴與作曲,年齡十七歲多一點。
一九六三年,時序進入初夏,音樂科裏正熱鬧滾滾的盛傳著一件大事,聽說美國國務院將派一位美籍奧國指揮來校指導管弦樂團。為了迎接這位大指揮,科裡的各管弦組同學比往常更緊張的勤練自己的樂器,每個人都害怕當指揮一到,有可能要求每一個人演奏一番,由此亦將訂定樂團的座位席次。這樣的事經高年級學長們的繪聲繪影,氣氛上顯得凝重,當時人人心中都有個疑問,到底從何準備起啊?
事實倒也不像預期的那樣可怕。一天下午適逢管弦樂課,鄧昌國校長和申學庸主任陪著一位身材看來高大,頭大,耳也大的白人來到課堂中。鄧校長等簡單介紹了來賓後隨即離去,而那位指揮一言不發,立刻發下一疊分譜,並拿起指揮棒毫不留情的揮將下去,一陣錯諤,弦樂組的同學趕緊拼命視譜跟上直到樂曲終止。一曲普賽爾(Henry
Pucell )的「姊妹情仇」序曲,在 in tempo 的狀況下奏完,此時每位團員都汗流夾背,但心中卻大呼過癮,這就是蕭滋老師帶給樂團的第一個見面禮,實際裏略帶著下馬威的意味。從此之後,每當有新曲目,蕭滋老師則如法泡製,毫不留情的考驗樂團的視譜能力與敏感度,從未有過例外。
從一年級到三年級,管弦樂課都擠在小小的合唱教室舉行,狹窄的空間,低垂的天花板,夏日裏只有大電扇沒有冷氣,音響效果也不高明,蕭滋老師從不嫌東嫌西,在氣溫30℃之下,揮汗與樂團排練,幾節課下來,略為胖碩的他早已渾身是水,但甜美的微笑從未自面孔上移開,在那裏我們學了很多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海頓、孟德爾松、布拉姆斯等作曲大師的無數作品。四─五年級後,管弦樂課改在獨立大樓的圖書館二樓,該館距離音樂科約有300公尺之遠,每回上課用器材如指揮台、譜架和分譜袋都得從音樂科辦公室運送到上課現場,極倍艱辛。當時這樣的工作都由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老謝一手承擔,他是搬運上課器材的幕後英雄。工友老謝只說台語,每一回蕭滋老師都會向老謝報以感激的微笑,老謝當然也只能回報蕭滋老師傻傻的笑容而已,這樣的畫面看在我們心中,成為一幅最美麗深刻的圖畫,永遠忘不了的真情。早期的音樂科因著學生數少,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極為密切融洽,那是一所令學生和老師(甚至工友)都同時能進步的學校,在那裏,蕭滋老師和管弦樂團的師生一塊兒成長,一塊兒學習,一同享受音樂所呈現的喜悅。當時樂團的水準獨步台灣,一群人不分大小共浴成長的幸福。
隨著歲月的推移,越來越意識到與蕭滋老師足足五個年頭的管弦樂課學習絕非只是一件偶然相遇的事,也絕對不是表面上的師生關係而已,它有著某些內在聯繫的因素。記得二年級下,我曾向他提出上指揮學的個別課,起初他不置可否,只淡淡的回說:「有空歡迎你每星期來我家陪我做管弦樂團的分譜。」於是每週一個下午我依約前往,第一次他正以紅、藍鉛筆和尺在一份全新的莫札特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分譜上劃各種記號,他一面劃一面遞譜給我,且立即解釋他所做的弓法與管樂的分句,並要求我一一在總譜上作對照。剛閉始我不明白上指揮課為什麼得先學會劃譜,礙於情面我只好照做,如此每週一次,每次數小時,我指揮課居然是陪他做分譜,由於他不收學費,還倒貼茶水、點心,因此這種課程持續不到一年半,就提前結束了。四年級之後術科加重,只好向蕭滋老師道聲謝謝就拜拜走了。事隔四十年回想起來,當初的我真是笨啊!因為我修作曲,而那些劃分譜的枯燥工作乃是蕭滋老師想藉此磨練我的分析能力罷了,雖然事到如今有點悔不當初,但已受益匪淺了。
被蕭滋老師指揮演出是一種極高的享受。每星期同學們都期待著管弦樂課的到來,懷著既害怕又興奮的心情前往上課,和他一起演奏音樂,使我們的琴藝變得更完美,演奏上更具信心,心靈方面有著更多的充實感,這種感覺像極了嬰兒與母親之間的關係,蕭滋老師總是深情的以母親般的手推動樂團孩子們在搖籃中的感情與真誠之心。年輕時候的我們在學習方面有些特別,一方面強烈依賴和模仿可信賴的老師;另一方面卻各自朝著自己的性向,往不同的方向發展。蕭滋老師從不在這方面給與學生任何意見,當每個人都熟知自己所擔任的聲部時,他會放任樂團肆意的放開腳步,而他的眼神和手勢往往令樂團在必要的時刻收回自己,大夥兒同心協力一起向前走‧‧‧‧。音樂方面,蕭滋老師的詮釋從不誇張,也不附加任何不相干的表現,他認為音樂是純潔的,任何附加效果足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皆不可取,音樂不可因著任何目的使其改變了原創的面貌,他認為音樂如能照其本象流露,其表現力已足夠且更具有說服力。蕭滋老師雖以英語授課,但我想私底下,他的思維一定是德語,因為德文這種語言很適合去表達某些抽象思維與哲理性思想。他待人處事如同帶樂團一般,一絲不苟中富於人性的真誠,和他一起練習一點兒也不會枯燥乏味,相反的,他的練習充滿了機智與活力,熱情中不失清晰的條理。
從現今的時空與觀點去回顧蕭滋老師的種種,難免會產生一些不甚合理的假設與幻想。我願盡力免除目前我身為職業作曲家的感觸,而讓時光倒回四十多年前小伙子的我,我盼望能盡力回想當時的感受,畢竟那五個年頭與蕭滋老師學習與相處的日子是何等真實又寶貴,在我心目中,他仍是我永遠的指揮。
作者按:蕭滋博士(Dr. Robert
Scholz 1902-1986)奧地利史泰雅市人,一九三六年間定居美國,是莫札特作品的權威詮釋者。一九六三起奉美國國務院之指派赴台灣講學及指揮樂團前後達廿三年之久。他後半生全心將自己奉獻給台灣樂壇,不但造就了數以千計的優秀演奏家,亦被喻為台灣交響樂團的偉大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