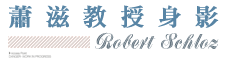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Robert走了,送他回家的是優美而憾人心弦的歌聲、樂聲,是主教、神父、親友、弟子們摯誠的祈禱;在莊嚴肅穆的大禮彌撒中,耶穌再一次在聖體聖血中,重行十字架上的完全的犧牲,但這次也是為了Robert,為接他回家,回到天父的懷裡。
能讓我同去嗎?我嚮往著的天鄉,能和你同登天父的殿堂麼?-多磨奢侈的盼望!你那八十五年紮實的歲月,我是望塵莫及的,愛與至誠,生活於基督內的精神,堅強的信心和信仰,都是我的楷模,是我今生努力的方向……。
民國五十年十二月我乘Asia郵輪,自義大利的拿坡里回國,巧遇不同國籍的神長們也搭此輪回亞洲各地服務,我和六位中國神長在一起,可以每天望彌撒,和他們一起唸經,唱聖歌……是最愉快的旅程,但是我的心境總是沈重的,「使命感」激發著我,每晚獨自一人伏在船尾欄干上,望著大海中的浪濤。靜靜的天空,晶瑩的星星,我的心與靈,在宇宙萬物中,託給了「主」;指引我方向吧,給我吧,親愛的十字架,為我的同胞,為我的國家……。
國外讀書的歲月中,時常思念著我的國家,受苦難的同胞們,我的童年是在全國一致抗戰的時代,同胞們的慘遭殘殺,傷兵們的呻吟掙扎,鮮明地烙印在我稚幼的心中,那時代的中國人激發了最高的民族意識,昂揚的愛國情操,懷著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偉大信念去奉獻、去犧牲、我雖幼小,卻有幸能在那時代中成長。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中句,師大期末考,系主任戴粹倫教授邀約剛到臺灣的蕭滋教授來學校瞭解些系內的情形,也聽聽同學們考試,那天先聽了聲樂組,到鋼琴組時,是上午十一點左右,順著編號考到一年級副修僑生,記得那位同學彈的是Chopin作品64之l,Minute圓舞曲,是快速瞬息在一分鐘內該彈完的圓舞曲,但那位同學慢慢的重覆再重覆,戴主任、蕭滋教授很有耐心的聽著,老師們感到不安了……終於彈完了,同學站起來鞠躬,蕭滋教授低頭看了下錶,會心的一笑,後來告訴我那位同學彈了約六分鐘,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Robert”。
暑假中蕭滋教授在美國新聞處舉辦鋼琴講座,一天接到他寫來的問候信,關心我害風濕的情形,是同學們告訴他的,他希望能給些幫助,對一位還不認識的中國鋼琴老師,他那麼有心的關懷。
葛樂麗颱風剛過,台北被風雨侵襲得零亂蕭條;我在教堂望過了彌撒,借打電話,那是一通出於感激的電話,我的聲音是愉快的,相信也是有感情的,「Hello,Dr.Scholz,Hello,」。聽筒的那邊只「Hi」了一聲,是靜止,然後我聽到低而遠的一句「Who
is calling, who are you?」我說:「Miss Wu, 接到你信的Miss
Wu……」,又無聲的休止,然後仍是低沈的一句「I would like to see
you……」。約定了星期日下午三點去看他,當時我感到的是「Professor absent
mind」,掛下電話,總有份不安。
Robert後來告訴我,在接到我的電話後,他感到非常的興奮與激盪,同時在心的深處昇起了種安全與平靜的威覺,這使他不眠不休工作了兩天一夜,直到星期日下午三點,後來富美在音樂的禮讚中有這麼一段記錄:「那話筒另一邊傳來的話語,宛若天上灑下來的一串銀鈴聲,比美天籟,蕭師整個人為之出神……那動人心絃的聲音,至今猶深深地印在腦海中,永不能忘」。這是Robert向主稅、富美說出的。
坐著三輪車,到蕭滋教授所住的弄口,車夫願意等,我說:「好吧,大約十幾分鐘」。雨後地面積著水,我注意地跨過去,抬頭時突然看到蕭滋教授在客廳的落地窗前,全神貫注的望著我,那種專一注目的光與力滲透了我的心靈,就在那一剎那,相信我們的魂魄都已離開了我們,超越了一切,感通在天地之中。
我不知道怎麼走進了客廳,彆彆扭扭的坐下,他更是彆扭的要我看看他的鋼琴,參觀他的書房,又把抽屜打開了,看看裡面裝的東西,好彆扭,我說要回去了,但他去了廚房,端出了一隻熱騰騰、剛烤好的大肥雞,請我坐下來吃晚飯-才過三點,他端著盤子站在桌邊,迫切的問我的名字,我說:「我是吳漪曼,Emane
Wu.」「還有呢?」「沒有了」,「請解釋一下」。我說:「Emane是我的名字,Wu是我的姓。」「喔!」問清楚後,他安心了……。離開Robert,三輪車還在巷口等著,等了一個多小時了,那也是我吃過最早的一頓晚餐。
心與靈的感應,超越了時空,是純情的,是來自上主的,是奇蹟……那麼的美,也蘊藏有那麼多的苦。
朋友曾勸過,想想看那不同的年齡……是的,但那靈犀相通的光輝,那心靈的震撼…那剎那已成為永恆!二十三年…在中國的歲月裡教學、演奏、著作,後半的十三年幾乎都在病痛中,一次次的從危險中掙札過來的。安和樂利的社會裡,欣欣向榮成長茁壯的樂壇中,生活是那麼的溫煦,有那麼多驚人的才華,才華的成長,專注投入的教學與所得的喜悅,是最好的酬報。這裡原本是純淨的樂土,這裡原本是真正的快樂仙島,有朋友們的關注和愛護,有求知者的盼望和勤奮。
然而生命的狂飆時刻隱伏著,一波又一波的襲來,二十四小時的緊張,分分秒秒的擔憂,盡一切的可能的維護,我守著,守護著他的「生命」十三年;從生命的邊緣一次次搶教過來,甦醒了,健康了,感謝醫生,感謝上主,再一次的,再一次的把他還給了我;而我心中那根緊拉著的弦,竟也能堅韌的承擔下來了,我是和他一同迫近生命的邊緣,和他一同在死亡陰影中掙扎,那從生命盡頭又扭轉回來的激動!現在,一切都靜止了,只有火在我心中燃燒,我沒有淚,也不感到累,我只感到我在燃燒,該哭的時候,我只有笑,我的淚呢?怎麼都乾枯了,因為生命在燃燒。
十字架,親愛的十字架,自第一次懂得它真正意義時,就被完全感化了-救贖人類的苦難,祂的聖體,祂的聖血溶入了我們的靈魂,滴進我們的血液中,跟隨著祂一步步登上加爾瓦略山-我早把Robert奉獻了,為了中華。
有一次,我真正的不安是一九七○年在日本,Robert指揮武藏野音樂大學樂團及合唱團,演出Anton
Bruckner的”Te Deum”那是場憾人心弦的演奏會,演奏者與聽眾,都連結在一起,我的心也深深激動著,突覺一陣刺痛,全身籠罩在不安中-台灣、台灣、台灣需要你,Robert,你怎麼會在這裡?我們怎麼會在這裡?淚湧出來,停止不住的淚,我在啜泣。一年後,我們回來了。
Robert真是個勇者,真是堅強,在這種健康狀況下,他仍完全投入的工作,思考追索,追索思考,真是在做全盤奉獻,他的心臟是如此衰弱,呼吸困難、肝臟、肺臟都積水,不能吃,不能睡,靠針藥排水;他常是閉著眼睛,靜止般的躺著,我就會輕輕的叫他,他即刻睜開眼睛,「你沒睡?-沒有-在想什廢?-音樂,我在背Mozart的Serenade。-你在指揮?-是的。-你不累嗎?醫生說你在危險期,你必需安靜休息,才能恢復過來。」他輕輕的說:「我在和我的音樂說再見;昨晚我背了Beethoven第一和第二號交響曲和Brahms的「大學」序曲,現在是Mozart的音樂……。」醫師憂慮的說:「為什廢他不能安靜下來?為什麼他不能好好休息?是什麼事情使他憂慮?」他靜靜的在無聲中,但在音樂狸,一次次康復過來。
一九七五年(民國六+四年)夏天,一次危險期中,他沈睡了一天一夜;後來告訴我,那是他最辛苦的經驗,在沈睡中,心靈在扭轉翻騰,金色的光,強而熱的逼迫著他,整個身體心靈都在掙扎,無休止地在步步前進,層層上昇;在無法再支持時,平靜突然降臨了,感到安定和舒暢。他很清楚,他知道,往後的日子,他必須這樣的辛苦,然後會獲得寧靜的安慰;他醒過來後,脫離了這次的危險期,從此他開始了寫作。
寫作是他最辛苦,最緊張,也是他最後生命的開始;有時靈感泉湧,他會說:「思想來得那麼快,來不及記,需要好幾個人來幫忙。」有時又日夜定住在某一點,扭轉不過來,全身像一根拉緊的弦;然後,他會好高興的說:「找到了,找到了。」他整天整夜的思考著,工作著,靈感來時,隨時寫下在任何他順手拿到的紙上,先用速寫的方式,然後打字;常會一改再改,一刪再刪。他生活的範圍漸漸縮小,要從海闊天空屬於世界性的演奏生涯,退到他房間的書桌上,這對他真是多麼的痛苦!但他沒有停止過一分鐘,躺著、坐著、靠著、吃飯時,上課時和朋友聊天時,病痛時,甚至到生命的盡頭時,他無休止的思索、探討、追求基本的理和道,各種學問的根源,把生命活動領域發揮,達到了最高?。
他坐在書桌前,望著窗外那小小的一片,春去秋來、冬至又是一年;我心痛的守著他,他的音樂世界,他的演奏生涯……他對宇宙萬物的愛……,窗外搖擺的樹枝,雨後的陽光,都令他幸福地微笑……,他的幽默感,他常會獨自格格的笑,「什麼好笑?」「喔!耀的香港腳,哈哈!」「郎世寧的駿犬-抓癢的狗……劉上校…哈哈!劉上校。」任何事都可觸發他笑,我也跟著他傻笑了起來。有時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條手帕,打個結,再打一個,再打再打,那是要自己記得的事,常常摸摸手帕上的結,提醒自己……。
醫生再一次告訴我:「蕭先生的病情很嚴重,假若能好好休息,他心臟的機能會恢復一些的,然後能保持一段時期的健康。但是他不停止的勞累,不能靜止的思索,整個人在激動著,我有些懷疑:「他真是在思索?普通一般人在八十四、五的高齡,尤其在這種健康情況下,是不可能清楚思考的,也許是一種幻覺,那是精神和健康的浪費……,希望他能安靜下來,希望他能休息……。」
我求他休息,也把醫師的話重說一遍,他出聲的笑了,「Oh no,我不是在幻想,不是在做白日夢……。」在他深沉的思考和掙扎中,他再一次次的恢復了過來。
我家阿巴桑看他一直伏案工作,不經心的對我說:「蕭老師這樣辛苦,以後會賺很多錢喲!」我告訴了Robert,他又笑了,「這一定不是賺錢的,也一定不是暢銷的,只是提供給專家學者們思考,也許會有幾本存留在圖書館裏,為有心鑽究的學者提供些見解……。」
他常有低潮,情緒上的低潮,總是在無聲的忍受著,偶然他會吐一句「唉!I feel
so low。」從他的眼神中看到他內心的煎熬,是寂寞,是無助,是不安,又好似在深淵裡;我總在房聞的另一角默默的祈禱著,因為內心的衝激是要從內心去平靜下來;他總能自己了悟開朗起來,開朗後,又把他新的收穫紀錄下來。一次看他悶著悶著,我實在忍不住了,蹲下去,我捧緊了他雙手緊握的拳頭,「Robert,看!我們在跳高前不是要先蹲下去嗎?等待著跳躍的奇蹟和躍升時的快樂吧!」我們對望著……。Robert有著澎湃而起伏的熱情;又有一次,看他在不安中,我也染上不安,再次緊握著他的雙手說:「讓我們告訴上主吧,憑我們的信德,上主為我們立下「告解」(confession)那是多麼美的聖事,從”confession”中我們更能體驗到上主的偉大和無微不至的愛,祂在傾聽徹悟了的孩子的訴說,然後祂說:「你平安的去吧!孩子!為你的補贖,你唸一段或默想一段經文」。補贖為使你更安心,經文使你更接近上主。是的,祂就是「寬恕」,就是「愛」,當對事物徹悟後,就要寬恕自己,把愛與精力投注於發揮,無謂的不安,是對自己的騷擾,是精力的浪費,我們要揚棄它。」Robert
沈默了,他望著我,他謝謝我……。他再進入深沈的思考中,然後充滿了靈感伏案疾書。在熱烈洶湧的浪潮裡,在不斷起伏的創作波濤上,他總在沈思中有所徹悟、躍昇。
他仍教幾節鋼琴課,專心的教,對樂曲中的細節,嚴格的要求著學生,對於音樂他的耳朵仍同樣的敏銳,但最大的困難是呼吸和體力,從房間走到客廳,就像是登一座高山,那麼辛苦;在辛苦了一天後的黃昏,他已很累了,以前總喜歡看幾分鐘中視的「大家一起來」節目,雖然不知大家在猜說些什麼,只是他喜歡看年青人的喜樂;然後要我把電視、電燈關掉。有時我會直覺的問一句「想睡麼?」「oh,
no I'm giving a concert。」所以我常要在摟下上課,為要給他安靜,那是他無聲的音樂世界,他在音樂裡,他在背譜,在指揮,每次安排了不同的節目;約九點左右又起來,伏案寫作,寫下他剛發覺的靈感!
感謝上主給了他那麼多的靈感,豐富的創作能力,那麼堅強的意志,能在老弱殘病中,把他的思想領域發揮到生命的巔峰。每次住院時,隨著教護車,我們總帶了大小箱子、手提包等等,其中一袋是Robert
自己親自檢查過的,他的筆記薄、幾支筆、橡皮擦、計算機和無線電,一本讀者文摘……,在醫院仍不停思考、寫作、他筆記簿上最後一頁8/28、86,之後幾天在他雙目幾乎完全模糊前的摘要中的最後一行寫著:Cogito,
ergo sum.Ich denke , daher bin ich Mensch(homo
sapiens)我思考,因此我是有智慧的人,智人。
在台大醫院的最後幾天,自八月底,凝固的血塊所產生的劇痛,使他不能入睡,強烈的藥物,使他不能進食,他和病痛在掙札,體力和精力都已耗盡,他以微弱的聲音告訴我說:「I
want to be dispersed,我希望就此消失,我的眼睛已看不清楚,耳朵也退化,我已沒有任何精力……。」「Robert你會好轉的,就像每次那樣,我們又會再回到家裏,你的書一定要完成。」「是的,希望再給我四個月的時間。」「當然,一定會的……」我那樣肯定的答覆著,但是,上主這次真的要你回家了,因為你已做了全燔之祭,完全的奉獻,你已給出了你的一切,那未完成的,也是最大的遺憾,你的「哲學思想」就讓敬愛你的朋友們盡一切的努力來整理結集起來,是的,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愛護你的朋友們,都會由衷一一來完成的。
你年青時代的十部作品,就將開始付印,準備贈送給樂團及圖書館。你在Henrystreet
Settlement Music School的清寒子弟中選拔而組成的美國室內樂團,你曾親自教育和指揮著他們演奏,一九五六年Westminster唱片公司曾把它灌製成的唱片,我們保存著;因年代較久和氣候帶來的一些損害,我們希望能克服技術上的困難,製作成錄音帶,予以推廣。
你的樂譜室裡,有你自一九三八年開始即付出許多時間心血收集的樂譜,在總譜與分譜上更有你精心的注釋,我們已在整理,雖然散失很多,但在這二十多年來確是提供了國內樂壇一些需要的幫助;為了大家方便,也為表示你對我國文化的尊重和對樂壇的關切,決定把這些和你朝夕相處了將近五十年的樂譜,贈送到國立中央圖書館,我要再說一遍「可借也很遺憾的是已散失得太多了。」
我們將用你的名義設立基金,希望從這有限的基金裏,真能做些為音樂教育有意義的貢獻。
這本紀念文集,多承師長和親友們惠賜鴻文,字字珠磯,篇篇都是至誠的感念,崇敬與摯愛。Robert
和我萬分的感激。親愛的Robert,僅僅感激是不夠的,唯有祈求上主賜福和保祐他們-每一位好心的、至誠的,我們的師長親友。
Robert,安息吧!安息在你所愛的地方;是的,我們沒有生長在這裏,但是我們都要埋骨在這裡,我們曾吸取過歐洲、美洲、亞洲的文化,我們要把這些高度文明,從我們生命的經歷中散發;我們以此為家,「家」那是有最多愛的地方--有真情摯誼的地方。「讓我葬在這裏,這裹有我最多的愛!」是你說的話。
Robert,再一次感謝你,感謝 上主讓我能分享到你的生命,和你生命中的光輝,分享到你的音樂,你創作的靈感和創作的泉源,你高昂的器度,你的道德,你的人品,你的嚴肅,你的幽默感,使我本來要哭的事,會衝出笑聲來;你敬業樂群,你達觀、仁愛和純真,你努力,你堅強,有不移的信心;你很獨立卻常會倚恃,你很成熟卻又很天真;你是歐洲的文化人,奧地利的音樂人,你是樂壇的播種者,中華民國的園丁。我是何等有幸,分享到這一切的-切,天主把最好的給了我,我,感恩吧,我的生命將延續在「感恩中」,努力活在純愛裏,作為我對所有關心愛護我們的每一位的感謝。
Robert,再請你,定要轉求上主,保佑所有愛你關心你的師長、親友、學生,你的祖國,你所鍾愛的中華民國,你是懷著對整個人類赤誠的愛的音樂人。
親愛的Robert,願我永遠能追隨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