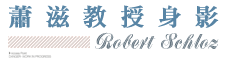序文
蕭滋老師(Prof. Robert Scholz)是在美國國務院的學術交流計劃下,於1960年代來台任教。他不但在當時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化學院和國立藝專等校的音樂科系擔任教職,同時也指揮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在這近三十年的日子裡,蕭滋老師對台灣音樂界影響之遠,耕耘之深,貢獻之大,到目前為止,未有一位外籍教授能出其右。事實上,蕭滋老師後半輩子的生命已融入台灣的土地。他不但與吳漪曼老師結為連理,共同致力於台灣的音樂教育,舉凡1960到80年代,本地音樂家的工作和生活,幾乎也都和蕭滋老師發生關連,從音樂幼苗到年近花甲的教授,蕭滋老師或為師、或為友,都與他們產生密切的交流。蕭滋老師的學人風範,更讓其他藝文界人士所景仰。所以蕭滋老師和吳老師的生活領域,擴及文化和一般社會層次。蕭滋老師更是深愛這塊土地,台灣是他選擇為埋骨的地方。
現在我們紀念蕭滋老師,每個音樂界的朋友,各有其懷念和追思的事物。但顯然蕭滋老師所遺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除了真摯,熱忱和作為文化人的精神典範之外,還有更豐富的部份,那就是他的學養,每個人都可以從個別受教科目和生活點滴中,去描寫與蕭滋老師相處的情景,唯獨對我很困難。當吳老師要我也寫一篇專文時,我的確不知如何下筆,原因在於蕭滋老師和我的關係很廣泛,過去我曾以〈安魂曲〉為題,細數蕭滋老師的教學和體恤年輕人的種種事蹟,但總覺得仍然無以描繪全貌,我和老師的關係較一般樂界朋友略有不同,我必須找到一個實際層面切入,才能見到核心,而非僅與大家一起寫一篇文章而已,這是我一直思索而遲遲未能下筆的原因。我在想:我是否能夠透過一次記述的機會,將蕭滋老師的一些理念和音樂觀,具體而有效地傳達給年輕的朋友,以幫助他們日後對音樂的詮釋,包括作學問的研究態度。
1963年,我第一次見到蕭滋老師來師大上課,那時我才大二,從那時起到我返國任教,甚至當過系主任,直到最後蕭滋老師離開我們,他的容貌幾乎沒有改變。這二、三十年的日子,除了我在國外的時間,蕭滋老師幾乎一路協助我成長,甚至在我面臨白色恐怖的政治干擾時,蕭滋老師和吳老師也勇敢地挺身護衛我,為我仗義直言,他們向當時的張宗良校長的一句話:「如果曾道雄受到政治性的迫害,將會引起中華民國音樂界的公憤!」,張校長才不敢剝奪我師大的教職。而在我經濟最困難而且又忙著一起排練〈費加洛婚禮〉時,蕭滋老師特別去函向文化大學董事長張其昀創辦人,要求撥給我專款補助,這是蕭滋老師最為感性和體察入微之處。我前後跟著蕭滋老師學德文藝術歌曲、學指揮,也在他的音樂會中,演唱韓德爾、莫札特的歌曲,在文大演出的歌劇〈費加洛婚禮〉時,蕭滋老師指揮,我就擔任導演、翻譯宣敘詞,並親自飾演劇中的伯爵;在貝多芬的〈費德里奧〉歌劇中,擔任典獄長(此劇最後沒演出)。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蕭滋老師一起教師大合唱課,我上星期五,蕭滋老師來上星期一,我同時也當老師的助理及翻譯。我們上過海頓的〈創世紀〉、〈四季〉,還有莫札特的〈安魂曲〉,我在教學中學習,讓我獲益良多。
在莫札特的〈安魂曲〉譜本上,蕭滋老師明確地仔細寫著各個樂句的詮釋要點,也在管絃樂總譜上,將配樂作適當的損益,尤其是莫札特未完成,而由其學生Sussmayer補作的部份。後來我看了很多不同指揮家對莫札特安魂曲的詮釋,但隨著年歲和見識的增長,才越發體認到蕭滋老師詮釋莫札特之深度和學術的權威性。至今我仍保留蕭滋老師指揮莫札特〈安魂曲〉的手記筆跡,它已成為我隨後指揮這個作品的範本。我第一次突破「二二八」禁忌,指揮莫札特〈安魂曲〉,以及在師大或到國外指揮這個作品時,都以蕭滋老師的記號去詮釋。我後來曾和楊波柏博士(Dr.
Jan Popper)學歌劇指揮,也到義大利席耶納,上過費拉拉大師(Franco
Ferrara)的指揮課,但實際上,都是由蕭滋老師個別課給我的基礎出發。而最具意義的是,在聖家堂追悼蕭滋老師的彌撒中,我更是含著淚水,以蕭滋老師筆記式的莫札特〈安魂曲〉譜本,指揮曉明女中管絃樂團和師大合唱團,來為蕭滋老師送行,作最後的禮讚。
前個星期,我在師大音樂研究所「歌劇與神劇作品研究」的課堂上,剛好也講到莫札特的〈安魂曲〉,我翻開那本破舊泛黃的譜本,上面仍然活躍著蕭滋老師生動的筆跡。突然間,一個意念劃過我的腦際:我何不把蕭滋老師對莫札特〈安魂曲〉的詮釋法,詳細的寫出來,讓年輕一代的學子和指揮家,演唱者來共享。蕭滋老師這個珍貴的音樂遺產,對他們才是學術上實質的幫助,也更能象徵學術傳承的意義。我把這個計劃告訴吳老師,吳老師聽了十分欣慰,認為這是傳遞蕭滋老師教育薪火最具體的方法,能使下一代音樂工作者直接受益,我們也希望經由這些譜本的敘述和解說,讓蕭滋老師的智慧和教育愛,得以長存人間,並豐富我們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