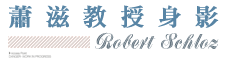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蕭滋博士比我早到台灣兩年。我到台灣不久之後,就得知有一位同鄉,一位著名的音樂家,也在台北。在那兩年中他已經結交了許多朋友,他們高興地接受他的邀請。雖然我自己不是個音樂家,但不久我即被列於他的賓客名單中,甚至成為少數能登堂入室的朋友之一。我曾與蕭滋博士和他的愛妻一起消磨了許多個夜晚。
往往在用過簡單但精美的晚餐後,羅伯和我就退到他的書房中,每次幾乎都談論一個不同的話題,內容包羅萬象。
我們的對談最早是從數學開始,或更好說是數字的象徵。「一」這個數字代表起源,「二」意味著二元論、兩極性、造物主和受造物。「三」意指無所不包的合一(unity),就像人類中的父親、母親和孩子,基督信仰中三位一體的天主父、天主子和聖神。
「四」則指向普遍性。指南針中有四個方位點:東、西、北、南。歷史分為四個紀(eon);在樂園中有四條河流。天主國的普世性,藉由站立在天主寶座前的四個肖似人形的活物,顯示給厄則克爾先知。基督信仰訊息的普遍性,藉著和基督一起被描繪出來的四位福音的作者而取得象徵,他們每一位有不同的面貌:天使、獅子、牛、及老鷹。聖熱羅尼莫在他們中看到瑪竇、瑪爾谷、路加和若望。
主要的行星有「五」個“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與木星。莫札特為木星創作了一首交響曲。談到這裡,我大膽地請羅伯對莫札特的一首幾乎不可能翻譯的清唱劇〈Die
Seele des Weltalls〉予以詮釋。但是羅伯不願討論莫札特其它這樣的創作,而且天色已晚,我們不可能討論所有的相關話題。
當我們進入數字的魔力這話題時,我想起我早先做過的聖經研究中,曾指出:創造的「七」天並非指一星期的七天,而毋寧是「完成」的意義。五位提了燃著的燈的童女並非成為婚禮的象徵,而是提醒大家明智的重要。魔力意味著令人著迷的吸引力,這讓我們很快聯想到莫札特的歌劇「魔笛」。至於「魔力」另一層比較陰森的意義,如妖術和巫法,我是不願意沾上邊的。
另一個晚上我們討論哲學,我們談到了希臘、阿拉伯、士林哲學和新士林思想。羅伯的知識最初使我驚異,但不久我就理會,我們兩人都幸運地受過相同的人文教育,沒有受現代哲學太大影響。
在下一次的談話中,羅伯問:人該對天主有什麼想法?對於他提出這個話題,我並不驚奇。我認為自己唸過四年神學,對這個問題可應付裕如。但是羅伯的第一個問題就擊破了我的幻想,他問道:「你能毫不加考核就贊同『天主是愛』這種說法嗎?」我答覆:「我從小就這麼相信的。」羅伯繼續問:「你早年對這愛的概念真正反省過嗎?」「當然沒有」我祇得承認,「但是經過七年攻讀哲學和神學,再加上數十年與人來往的經驗,我肯定認同。」羅伯說:「你或許是對的,但我仍不能了解天主怎麼能對某些她先前所深愛的人施以永罰。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跌入陷阱。幸好事實並非如此。天主無需積極主動地做任何事。她衹是沒有阻止她的受造物去傷害自己,然而她不斷反覆警告他們別這麼做,他們卻沒聽進去。如果天主的方式不是這樣,她等於剝奪了她聰明的受造物的自由。」這問題無法一次討論完,因此「人的自由」很可能成為我們下次會談的主題。
但是不久我親愛的朋友得了重病。我再次去探訪他時,發現他的問題已不再困擾他了。事實上,這不過是個為許多聖人曾受到的誘惑:擔心自己失去天主的寵愛。這種經驗幫助了羅伯和許多人,去更深的體會他們對天主的渴望。
我出席羅伯在台北聖家堂舉行的葬禮時,不禁感動泣下。他的朋友們為他做了最大的好事一用莫札特未完成的安魂曲來向他道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