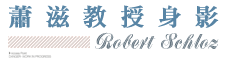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這篇文章是由遠自高雄,專程北上的彭浩德博士與傅樂文先生共同討論蕭滋教授所留的哲學性的遺稿的記錄。
此報告原為德文,經譯成中文;以饗各方讀者。
此篇文章的旨意,不在於學術性的分析蕭滋教授的思維及著述。因為真正的學術性論述是要參閱蕭滋教授的所有遺稿加以整理分析後,才可獲致的。所以祈望熱心的讀者耐心地等待。
蕭滋教授生前幾年來所結交往來的朋友以及共同討論的專家學者,他們一致同意其精神思考是他一生中極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本身也將此自視為其生命中活動領域的最巔峰。
在晚年裡,他的內心充滿著作曲的靈感與豐富的創作力。但另一方面他自忖一切的作曲不過是一種將「本」形諸於外的「用」。因此,深信唯有無止境地探索、追求基本的道理和觀念,才能臻於生命最崇高意義。
在古典音樂家裡,如巴哈、莫札特等及至百年前的作曲者皆深深地通達音樂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哲理。許多次,蕭滋教授遺憾的表示:這種根本的哲理已漸失傳,為人所忽視。而在此我們了解蕭滋教授的思想與觀念,不只是針對著音樂家,更是為了各種範購的專家學者而言。他自己曾將此含蓄地稱為「思想的啟發」。
身為優異傑出的鋼琴家,J.S.Bach:Kunst der Fuge(為巴哈賦格的藝術改編的「管弦樂曲」)的編輯者,作曲家、指揮家、音樂教育家,二十世紀音樂界名人的知己,世界各地的音樂天才的資助者的蕭滋教授並不以此自足,反而更自勉於精神領域的思考與追求。
思考領域
只要我們稍加涉獵蕭滋教授的著述,就會發現他所提到的內容涵蓋了人的行為和思想領域。
蕭滋教授曾說「我是一個音樂家,連在思考工作中,我依然是一個音樂家。」但,不幸的是有人卻因此將他的思考領域給予狹義的詮釋,這使他相當憤怒。因此對他而言,音樂之道即宇宙之道。因此在他的論述裡實在是包涵了整個宇宙的知識。如數學與幾何學、哲學與心理學、政治與社會、社會科學、物理學、語言學、歷史與宗教等。
在七、八十年代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是一個時髦的專有名詞,當時有許多專家學者在擁有龐大資金的組織之下建立了這方面的研究所、學會等等,藉此尋求各種不同知識範圍所需要的彼此溝通的基礎。蕭滋教授捨去這種思考的途徑而獨自採取自然的方法。從其豐富的音樂生活經驗,創作與思考之中,賦予日常的語言、詞彙以新的觀念與意義;另一方面則不使之失去原意。以此提示來傳達其「提示」與「思想啟發」。 研究方法
那麼,蕭滋教授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呢?又讀者在接觸其思想時所發生的困難何在?所有認識蕭滋教授的人士皆知他平生的言行,均發自其音樂經歷、無限的愛心,全副精神的奉獻,一顆憐憫慈悲的心;如泉湧的靈感,及其所謂的Bildnis。
他整個思想都來自於內心,並且一直不斷地在尋找一種適當的表達方法。他研究空間與時間的問題,是否因為他經過這些層層的嚴密思考,而使他的靈感如變調似轉化成語言呢?
在他尋求適當的表達方法中,曾遇到許多難題,雖然他並不喜歡使用專有名詞來解釋,但終就還是不得不使用;而在此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創作自己的詞彙。
他是如何創造他的詞彙呢?
他把普通日常用語加以「轉化」,賦予另一個新的觀念,使我們能隨著詞語的轉化而拓展更寬廣的角度及新的解釋方法來探究事物的道理。
使人敬佩的是他以無比的用心和嚴肅的態度來研究所有詞彙的細節。他運用詞彙時的謹慎之心可說到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境地。以音樂家敏銳之心特別注重詞的聲韻及詞根來源,然後再小心翼翼地選擇某一個詞當作他的專有名詞。
在尋找專有名詞方面,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有些詞甚至經過幾年的思考才得知。一旦發現,他即如孩童般地雀躍不已,無論三更半夜地打電話給朋友報訊:「我剛剛找到它了。」。而他是時常“有所找到”的。
在他非常仔細地研究詞根來源過程中,以拉丁文與日耳曼及其相關語系的詞根來源。而為了找到他所認為適當的表達方法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文法哲學。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靈感是支持他最大的創作力。因此蕭滋教授所分析出來的意義與詞來源經常與學術性的語言學有所差別。然而學術性的語言學家有時不得不承認他的音樂家之心的說法確有可取之處。
他的表達方法常常是把兩、三種象徵意義如簾幕般地層層掩上,想探究他的著述內容必得先掀開層層布幕才得窺見真意的殿堂。
唯有經由德文才能真正地把握住其思想的精髓,因此他的著述是以德文寫作。而這也正是令一般讀者難以了解其真意的原因之一。 思想境界
於樂理專家而言,蕭滋教授對音樂的數學性的會意是可明瞭的。在此我們無須論述。
蕭滋教授所謂的「信」、「志」、「問」、「省略」、「亂」、與「規」、是怎樣的?
當我們正視蕭滋教授的思考成果時,我們目前無從知道他是如何開始其艱辛的思考歷程及所遇到的難題。因為他總是流露出可親而令人信服的態度,與我們分享其思考的碩果,而獨自承受著思考時的苦澀與挫折。
現在我們大膽的假想,蕭滋教授在研究中所可能會提出的一些問題:
我為什麼問?
我為什麼有一個musikalische Frage?我問什麼?
我如何問?
我為什麼需要答案?
問題跟答案之間有沒有什麼關連?有關連的話又是如何?
在問題之前有什麼?
我憑什麼確定我所提出的問題是有答案的?什麼叫做「起源」?
「起源」和「開始」有何分別?有起源必有「終結」嗎?
兩者之間的發展「趨向」又是如何?其中沒有「規」?
有「規」的話,何謂「亂」?
如此一來,繫衍出的問題猶如鉸鏈般地緊扣著。有所提出的問題,皆有其共同的目標:反省與創造音樂經驗。
創造音樂在蕭滋教投的思想中與創造生命一致。
蕭滋教授曾說「上帝創造宇宙與人時,是以音樂之道而創造的」。
跋
初步的整理與略讀蕭滋教授所留下的遺稿尤其是記載思想方面的札記中,尋獲了其最後親手寫的字句,由其筆跡裡已可看出日漸衰弱的病體。此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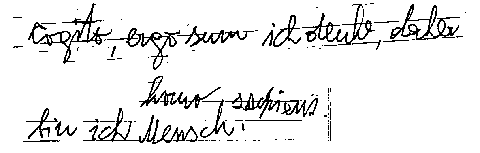
蕭滋教授的德文翻譯與註釋為:
Ich denke, daher bin ich Mensch
他將Mensch解說為homo sapiens
令人難忘的蕭滋教授是今日世界裡難得一見的他自己所謂的「Mensch」。
他不僅是一個“homo musicus”,音樂人,而且直到生命最後的一剎那,他仍然是一位「homo
sapiens」勇於追求真理的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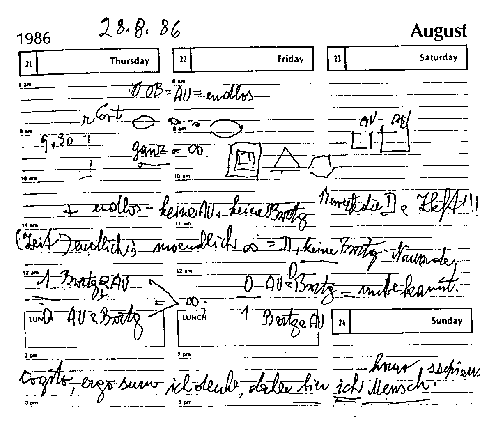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