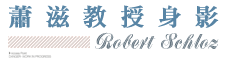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在蕭滋教授紀念專輯《這裡有我最多的愛》第45頁,有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的〈師道的樂章〉一篇紀念文,文中記載著:
「蕭滋教授以『教育家的形象』為題致詞,每一位在座聽講者無不深為感動;會後教育部朱匯森部長曾交代筆者將這篇講詞整理出來,印贈所有師範院校做為學生課外讀物,認為最能表達師道的醞義‧‧‧。」(〈教育家的形象〉這篇講詞,紀錄在《這裡有我最多的愛》紀念專輯第29-32頁。)
筆者有時去大百貨公司逛逛,經常看到有幾位小姐,穿著制服排列在門口,見到客人進來,便說一聲「歡迎光臨」,出去時說:「謝謝光臨」;我每次感覺到,他們是在奉命扮演這種「角色」。他們能說的「歡迎」或「謝謝」是否出自內心,令人質疑。但他們為了一份職業,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蕭滋教授在那篇講詞中,由其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意識,把教師和教育家清楚的、強力的區隔開來。他說:
「教師是把現成的知識,不關痛癢地,客觀地介紹給學生。是學生自己去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這種知識,雖然他們應當接受。教育家要做的多,多得多;介紹同樣的知識,但灌注著一種熱情和推動力。這推動力使他當初選擇這種知識,作為自己主修的科目。其實,他自己完全沒有選擇,是那科目選擇了他;實際上,就是他心目中的形象,使這門科目成為他自己的科目。」
蕭滋教授非但注意科目的形象,尤其著重在教育家的形象,且更要把真正教育家的形象給學生們。
為此,他先為自己指定一個方向,常記著自己是以傳爾布萊特(Fulbright)交換教授的名義前來中華民國,致力於加強他音樂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藉以為美國和他的祖國奧地利的形象有所貢獻。(頁31)
他忘不了幼年時的名師Wuhrer和Petyrek二位的形象。他從他們那裡得到的啟發,如何區別教師和教育家;他要像他們那樣不但做一位教師的「角色」,更要成為一位教育家的形象。
他又從學生的勤奮練習,殷切求好。對他流露的一片信賴,使他不得不成為教育家的形象。他說:「家長把孩子托給我,孩子又把自己交給我,這種信任,這種情誼,又隨著學生的成長而發展著;如此,教師便成了教育者,學生心目中的形象。」
他又從教育家(Educator)自拉丁文的動詞 "Educare"
來分析。這 "Educare" 有 "to bring
up" 和 "to lead out" 兩種意義,即成為一位教育家,必須給學生一個明顯的方向和對這方向前進的推動力。他說:「目標和教育家和信念融化成一個形象,這形象又在一個明顯的方向上引導著人。」
蕭滋教授二十餘年來對台灣音樂教學的貢獻,不僅把台灣音樂水準的質和音樂人才的量提升了,尤其給了教育界一個典範:要求自己成為教育家的形象,他教學的目標,是指導、訓練,並對每一位學生擬定一種計劃,使該學生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鋼琴家;他要求學生非但完全忠實於所演奏的樂曲,先要他們正確地吸收樂曲的精神,然後再以最圓熟的技巧表達出來;這是他自己學習並成為教育家的經過,並願以此傳承下去。他對年輕一輩的鋼琴家,「認為他們的技巧都很足夠,但總是缺少一種足以動人的格調與美感,有一種音的冷漠,使人聽後很難留下印象。」。(參考陳主稅,〈音樂的禮讚〉,載於《這裡有我最多的愛》紀念專輯,第86頁。)
筆者對音樂的門外漢,一竅不通的,除抄襲專家們的高見外,對蕭滋教授所提教師和教育家的區別,深深有感。他殊不願教師只盡到其為教師的角色,更願他們在學生和學生家長們的心目和感受中,給予一個真正教育家的形象。
教師不能忘了自己是個「人」,所面對的學生也是個「人」;「人」有理性生活、心性生活和靈性生活;因此只傳授理性中的知識,即使是最好的,是不夠的;還要把心性生活中的愛、熱誠、關懷灌輸給學生,更要把靈性生活中的理想指示給學生,帶領學生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的教師,才是一個教育家。蕭滋教授一生的言行和教育工作把這三者都做到了,所以他真正是一位大教育家,是他才有資格來區分教師和教育家,他以身體力行,給人們樹立了真正教育家的形象。無怪朱匯森部長認為他的<教育家的形象>這篇講詞,最能表達師道的涵意。
在我們紀念蕭滋教授百歲冥誕的同時,得感謝他給我們留下這篇講詞,尤其感謝他留下的真正教育家的形象的典範。這又豈止為音樂教學而已;如醫師、護士、宗教家、慈善家、社會工作者和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有澄清角色與形象的區分,致力於造成教育家的形象,而感謝蕭滋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