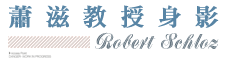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如果我們把時間的巨輪往後推,回溯至二十三年前-即民國五十二年,然後再把鏡頭對準台灣當時的音樂界,顯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番貧脊的景象,一片尚待開墾的荒地。國內僅有的一個正式樂團兩個稚齡的音樂系,及一些零星的個別音樂工作者正像一群牙牙學語,走起路來搖搖幌幌的嬰孩般,受著已持續近百年的狂飆似的西方文化衝擊。在當時政治、經濟、人文、地理等各方面條件極為有限的情況下,企圖摸索出一個方向,走出一條大道來。當時的有識之士均體認到要發揚國樂也好、西樂也好;要提倡音樂國際化也好,音樂現代化也好,均不能不從西樂著手。這並不是文化霸權的問題,而是人類啟智過程必經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的某些領域-有其歷史上的特殊原因-由西方人(特別是十六至二十世紀的中歐諸國)領先開拓。中國人在五、四運動之前即已領悟到文化腳步的前進不能繞過或忽視西方人已開拓的這一片繁榮、複雜而多元性的沃土。因此,”留學”這個現象開始出現。但是遲至一九六O年代,從台灣到歐洲學音樂的人仍然為數極少,僅帶回來有限的學識經驗。況且大部份的人均是成年後才出國,留在國外的時間最多也才十來個年,他們的背後又沒什麼世代累積的音樂傳統-無論是家庭的,亦或社會的-支撐。因此,能把音樂方面的表層工作-多屬技術層面的-學到融會貫通的程度已屬難能可貴,何能談得上音樂哲學內涵與文化紮根的層次?一九六三年的台灣樂壇仍有一大群人靠著極有限的資料,獨自摸索前進。也就在這一年,美國國務院作了一項對往後二十年的台灣樂壇有極大貢獻的決定-派請羅伯‧蕭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來華!
蕭滋老師時年六十一歲,體力很充沛、精神旺盛,有著熱烈的情感及音樂上的全面智識-包括指揮、鋼琴、管絃樂、室內樂、作曲及理論各方面,集四十年演奏與教學經驗於一身,還有這些才能表象背後的人生智慧及善良,幽默、勤奮不懈、樂善好施的人格本性。在我的印象中,蕭滋老師來到台灣後並沒有發生任何地域、國家或不同民族的心態認同問題。可能他唯一認同的對象是音樂及藝術工作吧。或者他的愛心包容了一切的不同與分類。不管如何,蕭滋老師當年即刻並且全心全力地加入了台灣音樂界的行列,帶領一群無助的人穿山越嶺,尋找藝術園地裏的樂土。其觸角所到之處幾乎涵蓋了整個台灣樂壇。他指揮省交,並任教於師大及藝專,同時指導室內樂團、聲樂、合唱、作曲及鋼琴的團體與個別學生。我當時經由父親友人高真民先生的介紹,很幸運地跟林惠玲、陳泰成、秦慰慈、汪露萍等同為蕭滋老師在台第一梯次的鋼琴學生,並跟當時在蕭滋老師門下學作曲的廖年賦老師及已故的張寬容老師共同演出室內樂曲。由於蕭滋老師的推薦與安排,台灣開始有一批學音樂的青少年遠赴奧地利、德國等地留學。人數由少而多,也帶動了留學歐洲的風氣。台灣教育界的音樂老師現有不少是留歐回來的,其中有很多優秀的音樂工作者均曾師事蕭滋老師,或間接受了他的帶領與影響。我現在回想跟蕭滋老師學琴那幾年,正值懵懵懂懂的年齡,只能約略領會老師身為經師方面的學識教養。我想他是當時在台灣唯一能夠有自信地解釋巴哈樂句及示範莫札特樂曲的音色與氣質的老師。由於他所處之時代背景及所受的正統、嚴格而深入的音樂教育,對理論的了解與演奏經驗的配合,還有本身才氣及近乎苦修士般自我惕勵的求知態度及率真的個性,使他在詮釋音樂與教學時不致陷入時下常聽到的一些運動成份佔很多、不是膚淺就是過份刻意地去作出,少有意境可言的音樂表現方式。我當時是無法了解這一點的,卻以孩童的直覺領悟出了某些“個中道理”,且後來當我的智性慢慢成長顯露,情與感逐漸溶化到靈魂深處時,這些我當時吸收到的養份仍未流失,它們仍在血脈中流動,成為我的音樂性的一部份。近年聆聽過的一些在台灣生長,目前活躍於國際樂壇的青年鋼琴演奏家中,個人認為以最近曾回國演奏的秦蓓慈最能讓人感受到蕭滋老師音樂的氣質與用意,在安穩的技巧之上,音樂自然流露,不誇張自大-演奏事業令演奏者容易產生的自我幻覺,也不小家氣-開發中島嶼民族容易染上的氣質。並且有別於一些純理性的音樂閱釋法更由於真情流露,不致顯得冷漠或過於尖銳,秦蓓慈五歲即受教於蕭滋老師門下,為時數年之久。雖說日後到國外又跟其他的老師學習,然蕭滋老師的音樂觀在當年的教化中也已微妙地溶入了小女孩的血液中。在這兒我想強調的是,蕭滋老師的音樂性不只是自然淳樸,同時因為他的出發點一直是為了追求“這音樂想表現的是什麼意境?作曲者想藉此傳達些什麼訊息?”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因此除了追求音色的美,音響的平衡與對比,速度的控制與捏放以外,尚有對個別作曲家的美學上的了解與想像,及不同時代所產生的不同思想體系、理念、哲學與宗教經驗的探討。我聆聽老師以前所灌錄的唱片。莫札特的一些室內樂曲,在那些音的脈動裡,有莫札特唯美的音樂理念,有莫札特嚴謹結構下的鮮明色彩,有莫札特奔放才氣之下的柔情,有莫札特率真、開朗的對話,有莫札特頑皮諧趣的調侃,有維也納RO
CO CO式的小巧玲瓏……蕭滋老師的闡釋樂曲,也是以唯美為出發點,並且已經觸摸到了作曲家的靈魂及時代的氣息。在我的想法中,這才是詮釋音樂作品應該達到的最高境界。我以自己今日對音樂的認知,來評價老師音樂性的內涵,愈能珍惜往日之所學。
蕭滋老師生長的背景-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奧地利,文人藝術家活躍,科學與醫學(尤其是心理學)發展蓬勃。政治上正值奧匈帝國Habs
burger王朝崩潰,第一共和國成立之際。奧地利內部政治紊亂,經濟窘迫,對外又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民生十分困苦,蕭滋老師曾跟我們提起,他童年時為了學音樂,如何地吃苦受難,常常半夜裏開始起程,餓著肚子走七、八小時的路程趕去上琴課。然後他又很得意的說,他常常把曲目練得如此之好,有一次他彈莫札特奏鳴曲,老師以為他就是準備了那麼一首,結果他一首一首接下去背著彈,老師聽得目瞪口呆。我還知道蕭滋老師有一個習慣,即清晨五點起來背譜,這個習慣他幾乎持續終生,一直到他被病魔擊倒為止。蕭滋老師個人的性格及他所處時代背景賦與他的價值觀,使他能夠真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位道地的音樂奉獻者,這一點尤值得我們作後輩的引為借鏡,以惕勵自己。今日物質如此豐碩,科技如脫韁之馬,以一日千里的姿態前進之時。我們回頭看看,心靈裏的功課,是否作了正面價值的交待?
我真正能夠了解並體驗蕭滋老師身為人師這方面的精神內涵與素質是在我成年以後,從維也納國立音樂院畢業回到台灣之時,那年蕭滋老師已年屆七十有六,身體不似先前硬朗,但精神上仍充滿活力、幽默、親切如昔。我們那時無論在那兒看到他,他的身旁總有吳漪曼老師陪伴著。大概因為我的先生是奧地利人的緣故,蕭滋老師常喜歡找我們去聊聊。語言的能夠溝通,加上隨著歲月成長而增加的對人性、事物的洞察力與理解,使我們跟老師及師母之間展開了一種亦師亦友,像長輩又像親人般的情誼。老師非常好客,在他還能行動時,時常邀請一些朋友、晚輩學生等饕餮一番。老師對吃非常有興趣,在他胃腸不好時,他只要看到別人吃得津律有味,自己也就心滿意足了。有一回,我們請老師來家裏吃飯,煮的是奧國菜,老師吃時不哼一聲,卻在幾天後於我們拜訪他之際,送了一本食譜給我們,我們三個看著食譜,然後均會心地笑起來。像這一類的事極多,老師的幽默感自有他的格調。我們從東海大學搬來台北定居以後,偶爾碰到老師身體狀況特別好時,就開車載他及吳老師出去走走。一次在大雨中去到桃園機場,老師戴著他的註冊商標-那頂深藍色的軟呢帽,在機場裏-套一句他自己的話-逛街。我們去得最遠的一次是台中,有時只到台北的某家大飯店。老師最後幾年最喜歡去,也是唯一能讓他稍微走動的地方就是大飯店裏較乾淨、不太吵雜,又不用擔心交通的有限的空間。但是,最後一年,他連這個小小的樂趣也被病魔剝奪了。他的生活空間慢慢地由橫跨歐、亞、美三洲的國際舞台縮小至他的住家,後來只能在廚房跟臥室之間稍微走動,之後,更縮小至臥室的床上,以及最後的台大醫院病房。他的體力也隨著活動空間的縮小逐漸消耗殆盡。然而令人吃驚的是,他的敏銳的觀察力與記憶力,甚至直感卻一直像泉源般,在他堅強的意志力驅策下,湧出新的動力,新的構思,新的想像。他晚年一直致力於一些很個人化的,主觀性的抽象思考創作,涉及到宇宙的諸般現象及語文學等。那個時期他雖已無力站在指揮台上,但是他的惱子裏仍尚收藏了無數的曲目-包括全套貝多芬交響曲。他說有時興緻一來,他會在腦海裏重溫一遍莫札特的丘比特交響曲,或貝多芬第八,或修伯特的“未完成”,或………。也有一次,他有點感傷的說:「我真想再指揮一次,再指揮一次……」我猶記得講這話時,老人的眼神現出憧憬的茫然,在那憧憬中,我似乎看到了昔日叱吒風雲的樂壇老將……。近幾年來,我越來越覺得能夠跟老師談話是一種福氣。老師的話題也越來越廣。只可惜,因為體力的關係,他有時講話極小聲,我不知因此漏聽了多少寶貴的,有啟發性的談話內容。他會講到世紀初至五十年代的一些音樂家及一些名噪一時的演奏家,其中有一些以老師歷史的眼光看來,是名不符實,另一些則受肯定。他也談到他的童年,父母親及哥哥Heinz,不過這些均屬較私人性的事情。關於台灣樂壇也談了不少。談到年青少年為了比賽,拼命練大曲子,且鬥得死去活來的現象,老師認為大家拼命想搭上巴士,這巴士開往的地方卻不一定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福地。老師極少批評個人,他僅把台灣樂壇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當作是文化過渡時期的陣痛。但是老師也有嚴厲的評語,有次他帶點悲傷的語調說:「台灣樂壇還有太多的半知識人。」語一出令人怵然心驚-在音樂的國度裏,他憂時憂民………老師極重視一個人對社會及人類貢獻一己之力的勇氣與能力,他說:「成熟即意味著能夠付出,能夠給予,而這是需要費力學習的。」……老師尊重星光閃爍背後那一群默默耕耘的人。他對藝術有絕對的信念,終生身體力行,在他身上,生命與藝術已結為一體……。老師是性情中人,他憎惡如仇……我想,我可以整晚坐在這兒,追憶老師生前的種種。雖說老師的長年臥病,使吳漪曼老師及一些朋友,學生們心理上對十月十一號這一天的來臨早有某個程度的準備,但當消息傳來,它仍然衝擊每個愛他、敬他的人如此之深。我深深感覺到,逝去的不只是一位良師益友,學高德重的長輩,同時是一位終生追求真理與音樂藝術,真摯地熱愛過他周遭的一切,並為他們付出極大心力的”人中人”!我心裏有一種愴然的哀傷、深恐跟著這位樂壇的牧羊人一起離開我們的將是某種深刻充實的人生觀、道德良知與藝術家的典範。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號下午三點,蕭滋老師在台北第一殯儀館入殮。望著躺在棺木裏老人安祥的臉,我們一群當日的學生情不自禁啜泣不已。一夕之間,跟老師的有形接觸已變為不可能,內心有種冰涼、寂寞的感覺。但是這幾天,當我的思緒與懷念一直繞著老師的影子打轉,心情由激動漸趨平靜時,突然領悟、明白了“死亡”即是“生命的完成”。一個人去逝後,他所說過的話,他所作過的事,他所傳達過的訊息即是他自身。他本人、他的永生不死的靈魂!蕭滋-一個啟智工作者,他來了,他播種了,他耕耘了,雖然台灣的音樂界現在並非滿園花草,但是也可說遍地綠芽,正迎著朝陽,勇敢的接受時代的洗禮與挑戰。我的老師,不,我們的老師,音樂界的老師,他的軀殼即將回歸大地,但他遺留下來的巨大精神遺產正以千萬粒小種子的形態隱伏在你、我的心、智、靈中,正在成長、正在播散。在這兒,人的小我顯得多麼微不足道,人類大我智慧靈性的延續像Phoenix(註)般·在死亡的熊熊烈焰中,從灰燼裏復活!!看哪,在那神性的萬丈光茫照耀下,永生鳥正驕傲地展翼而飛!!!
羅伯.蕭滋,以他肉身的死亡,印證了生命之不朽。
註:Phoenix:古代傳說中的永生鳥(或稱不死鳥)。當它感覺即將死亡時,即自焚,然後在灰燼中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