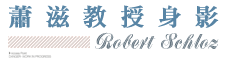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想起蕭滋教授,常令人重溫中國的近代樂教歷史。記得上世紀前葉與後葉,恰好有兩位可敬的外國友人,他們以雪中送炭的襟懷,將自己一生所學甚至餘生,奉獻給中國現代音樂教育渾沌初開的啟蒙時期以及因內亂兵災導致青黃不接的艱困時期。前者是二十年代上海音專的先賢梅百器(Mario
Paci. 1878-1946),他創建上海交響樂團,也開啟了中國學生鋼琴、管弦樂、理論、作曲、指揮……等全方位音樂的智庫。以最後二十三年的生命巔峰得中華英才而育之,直到終老斯土。
無獨有偶,美事成雙,後者便是我們最熟悉的蕭滋教授(1902-1986)。他是六十年代政府遷台後,我國樂教正陷於青黃不接的困境時刻,老天賜福,他來到台灣。從民國五十二年到七十五年八千多個日子,恰好也是他生命巔峰的二十三年,從早到晚亦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誨人永不言倦。他對我國樂教的貢獻,就像春風解凍一樣,以他德奧傳統的理論思維與歐洲古典的人文智慧為我們解惑,貫通中西歷史地理的時空心障,融會文化藝術風格情趣的歧異;以愛心傳道,細心授業;引領我們探索巴哈、莫札特的堂奧與鋼琴技法及管弦樂演奏的底蘊。他心細如髮的指導與幽默風趣的神采,跨越了語言的鴻溝。師生之間共通的語言就是音樂,使得音樂教育上的許多問題,透過薪傳的種子功能,都能逐月逐年,由壞變好,從好變得完美。非但贏得學生的崇仰敬愛,也贏得我們樂教同仁的欽佩與愛慕以及家長的感激。因為有他參與我們,和我們融為一體,當年我們樂教,才得枯木逢春,直到今天花香果甜。
蕭滋教授與夫人吳漪曼教授的教學生涯,跟我國古代顏回當今從事教職的國人一模一樣,典型的「窮教授」,卻也是標準的「杏壇夫子」。他非常崇拜孔子,對台灣尊師重道的良風美俗感受亦深,所以他曾詮釋「教師」與「教育家」的不同,「教育家」必須富有熱情與自發的推動力,要讓學生求學的意願發自他自己的內心,「我們教育了學生,學生也成就了我們」。由此可見,他與我國傳統經師、人師全方位春風化雨的師表典型完全相同。並不因他來自歐美而分軒輊,這大概就是我們大家特別懷念他的緣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