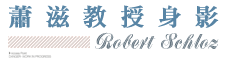|
(一)
在中國新音樂的歷史上,如果從一九○○年算起,曾經有許多外國音樂家居住在中國,他們各自在自已的專業上對中國音樂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貢獻。在一九四O年以前,受到各方認定貢獻卓越的,可以數出梅百器(M.
Paci),薩哈洛夫(B. Zakharoff)、富華(A. Foa)及齊爾品(A.
Tcherepnie)。梅百器,不僅為中國創立了一個極具水準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他也教導出像沈雅琴、董光光、傅聰這樣出色的鋼琴人材;薩哈洛夫與富華,為「上海音樂院」奠定了穩固的鋼琴與弦樂教學的傳統;齊爾品則以他的睿智,喚醒了當時中國人對本國音樂傳統的重視。一九四○、五○的二十年間,由於抗戰及內亂,無法在這一方面加以判斷。然而在一九六○、七○,乃至於八○年代上旬的二十五年間,對中華民國音樂發展有極大貢獻的「外國」音樂家,影像最鮮明,也受到各方一致推崇、肯定的,卻祇有一位-那就是來自美國,原籍奧國的蕭滋教授。「蕭滋」在台灣前後二十三年。他不僅被公認為是鋼琴教學方面的權威人物,而且對台灣各學校及職業交響樂樂團也有特殊的貢獻,他不僅讓台灣樂壇真正地認識歐洲音樂的傳統,也讓台灣的音樂界真正地體會到莫札特音樂的美。而最重要的,卻是在這二十三年間,他給台灣一音樂界樹立了一個「音樂教育家」的典範。
(二)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羅拔特‧蕭滋(Robert Scholz)生於奧國的一個小鎮史泰爾(Steyr)。早年音樂的基礎來自於母親及哥哥漢茲(Heinz
Scholz)。蕭滋的少年時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那段被他稱之為「飢餓苦難的歲月裹」,蕭滋所渴望的,卻是一位能指導他的鋼琴教師。他的「苦悶」,直到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三年,才得到了舒緩,他說:
「直到一九二一年,我才在維也納上了大約十次的鋼琴課;同年秋天在薩爾茲堡(Salzburg)的『莫札特音樂院』(Mo
zarteum)又上了十次。」而那二十次課,卻是非常辛苦得來的。史泰爾離維也納將近一百六十公里,在那時交通並不如現在發達,蕭滋得坐五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抵達維也納以後,與當時的名師沃賀爾(Wuhrer)一口氣上五個小時的課,上完課又因為火車轉接的關係,往往要在第二天清晨才能回到家中。而且由於戰後物質貧乏,每次的旅途,也都祇能以一兩片麵包夾果醬來充飢。蕭滋的二十次鋼琴課。每次都是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完成的。然而這種因艱苦才能得到的鋼琴課,卻使他更珍惜這每兩個禮拜一次的學習機會。每次跋涉之前,他都能盡力把功課做得盡善盡美。也是這種艱苦學習的經驗,使得蕭滋在日後教學之時,特別用心地使學生能獲得充分的教導。
一九二○年,蕭滋在「史泰爾學院」(College Steyr)畢業。翌年考入薩爾茲堡的「莫札特音樂院」,一九二二年即以特優的成績獲得了鋼琴與理論的「音樂教師證書」。之後,蕭滋即開始了音樂教學與演奏的生涯。從一九二四年開始,蕭滋與胞兄漢滋一同致力於雙鋼琴的研究與演出。蕭滋兄弟在一九二○、三○年代以雙鋼琴在各地演奏的名聲十分響亮。他們的名聲延至七○年代,仍然有人提及。然而,使蕭滋兄弟名聲更上一層樓的,卻是在一九二七年間,名聞世界的樂譜出版公司-維也納的「環球公司」(Universal
Edition),委託蕭滋兄弟,根據莫札特的手稿,整理編定一套完整的「莫札特鋼琴曲」。初版於一九三○年問世,立即受到樂壇的重視。蕭滋兄弟不僅被認為是「莫札特權威」,也開了「根據手稿」編定古代作品的先河。
一九三○年代,歐洲樂壇正瀰漫著「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的浪潮。「回歸巴哈」(”Back
to Bach”)的口號也十分響亮。一九三四年四月·蕭滋兄弟在薩爾茲堡以雙鋼琴演奏了巴哈最後的傑作「賦格的藝術」(”The
Art of Fugue”),演出的成功,轟動了整個歐洲樂壇。樂評家一致認為是音樂界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後,蕭滋兄弟每年都應邀在薩爾茲堡音樂節演出這首樂曲,直到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攻佔奧國,蕭滋遷往美國定居為止。
蕭滋兄弟在活躍期間,經常與當時的大指揮家合作演出,如克萊門‧克勞斯( K.
Krauss)、華特(B. Walter)、密特波洛斯 (D. Mitropulous)
、托斯卡尼尼(A. TOscanini)及卡拉揚(H. vonKarajan)等人都與蕭滋兄弟合奏過。這些經歷使蕭滋兄弟晉昇為一流演奏家的行列。一九三七年,奧國政府頒給蕭滋奧國國家音樂教授的殊榮,以獎勵他多年來在音樂上的貢獻,接到這個榮譽時,蕭滋正在美國作巡迴演奏。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莫札特生前演奏的薩爾茲堡主教大廳,隆重舉辦重啟莫札特自用鋼琴演奏會中,蕭滋被選為唯一的演奏者,並向全世界廣播。
翌年,蕭滋受聘為紐約「曼尼斯音樂院」(Mannes College Music)的鋼琴教授,同時亦任職「亨利街音樂院」(Henry
Street Settlement School)。這兩所音樂院的性質迥異,前者是以訓練音樂的專門人材,並且授以學位;後者的財源來自慈善機構及富商巨賈,目的是使家境貧寒卻有音樂天賦的青少年也能有一流的學習環境與一流的師資教導,錄取的學生學費全免,但卻無學位的授與。美國頂尖的鋼琴教育家凡戈娃(I.
Vengerova)及出名的小提琴教師賈拉米亞(Ivan Galammia)等都曾在「亨利街音樂院」任教過。也是在「亨利街音樂院」中,蕭滋開始接觸指揮,並且與當時也在「曼尼斯音樂院」任教的大指揮家塞爾(Geroge
Szell)學習,亦向當時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指揮的華特請教。一九五○到五五年間,蕭滋組成了一個職業性的「美國室內交響樂團」(American
Chamber Orchestra),賈拉米亞、普瑞幸格(Presinger)都是團員,這個團體在五年之內名噪一時,曾經錄製許多莫札特的唱片。後雖因故解散,名聲卻持久不下。蕭滋在一九五一年以前曾經先後寫過十二部作品,其中包括一首交響曲(Symphony
in E ,1951)二首管弦組曲 (1932 , 1935),一首為雙鋼琴的「前奏、聖詠,小賦格與展技曲」(1924),一首雙鋼琴協奏曲(1928),及改編巴哈「賦格的藝術」的管弦樂曲
(1950)等。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蕭滋在美國教育基金交換計畫下,奉派到我國。
(三)
一九五○、六○年間,曾來台灣演出的世界一流音樂家雖然稀少但也能數出瑪利亞‧安德遜(
Marian Anderson)、魯道夫‧塞金(Rudolf Serkin)、葛理果.·彼雅特高斯基(Gregor
Piatigorsky),甚至於「波士頓交響樂團」及「辛辛拿提交響樂團」。但是,他們都如蜻蜓點水,激起了一點漣漪,又歸平靜,對台灣樂壇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影響。而蕭滋卻被這裏充滿了「驚人的才華與熱忱」(”Fantastic
talent and enthusiasm”)的學生吸引住了。更或許是台灣當時音樂教育的「困境」,使他想起了自己少年時代渴求獲得正確音樂指導的苦悶情懷,而因此激發了他「教育家」的熱情,使他在各種條件,設備都不足的環境中,下了留下來的決心。而他的決定,如今看來,的確是台灣樂壇的一件大事。蕭滋到台灣以後,立即應聘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鋼琴與合唱,同時任當時仍在台北的「省交響樂團」客席指揮,前後兩年。在這兩年間,他為「省交」引進了許多以往不曾演出過的曲目。同時蕭滋也在當時的「美國新聞處」舉辦了一系列的鋼琴講座。他以講解、示範、分送講義、個別指導、介紹樂曲等,來助長當時鋼琴教學的水準。蕭滋的「講座」使許多鋼琴家對鋼琴、鋼琴演奏、及鋼琴樂曲的認識耳目一新。蕭滋也在同年應聘「國立藝專」,擔任音樂科的合唱及管弦樂團指揮。面對已有七十位團員但程度不一,良莠不齊的「樂團」,蕭滋接手後,立即裁編為十九人的室內樂團,從指導一人練習開始,以至於兩人同時練習,再至分組練習,然後兩組對練,最後才一齊合奏。他的方法,使「藝專管弦樂團」在短期內獲得驚人的進步。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以往認為祗要「人多就能成團」的觀念。
二+三年來,蕭滋除了在一九六九年應邀返歐指揮「柏林交響樂團」,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短期赴日本「武藏野音樂院」任客席教授,及到漢城客席指揮以外,一直留在台灣。他先後任教師大、藝專、文化大學,並且經常客席指揮「省交」與「市交」。一九七五年從教職退休以後,他仍然從事鋼琴教學及音樂研究。一九六九年他與我國傑出的鋼琴家吳漪曼教授締結良緣,蕭滋也因此正式成了中華民國的「半子」。從蕭滋首次抵達台灣開始,他雖然為台灣樂團及合唱團引進了許多新的曲目,為國內樂壇的演奏拓寬了領域;但是這二十三年來蕭滋對國內樂壇最大的功績,要數他培育了無數優秀的鋼琴演奏及教學人才,國內近幾年來鋼琴水準得以提昇,蕭滋實在功不可沒。他同時也為國內的音樂教育家樹立了一個典範。提到蕭滋所栽培出來的鋼琴人才,信手拈來,目前活躍於國內音樂界的有:張瑟瑟、葉綠娜、林惠玲、劉富美、蘇恭秀、彭淑惠及甫回國的黎國媛等人;在國外活躍的,也有陳泰成、陳芳玉、陳淑真、秦慰慈、秦蓓慈、薛嶺寧、王愛梅、劉杭安等。而這些祗是幾位代表性的人物而己。蕭滋的學生,出國進修時都有優異的表現,他們不僅在各地的比賽中頻頻得獎,在學校中也都有優異的表現。這些都顯示出蕭滋在鋼琴教學上傑出的能力,以及他把台灣鋼琴演奏水準提昇到近乎國際水準的明證。
(四)
蕭滋的學生眾多,但是每一位受教者,對他都自然地擁有一份發諸內心的敬愛之情。今年的五月下旬,幼時受教於蕭滋,目前任教於「茱麗葉音樂院」的鋼琴教授康寧(Martin
Canin),還千里迢迢地專程自紐約來台北探望蕭滋。是什麼力量造成的呢?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蕭滋在「文化建設委員會」為「慶祝蕭滋博士來華二十週年」的宴會中致詞說:「教師祗把現成的知識,不關痛癢地,客觀地介紹給學生。學生自己決定接不接受這種知識,雖然他應該接受。」教育家要做的卻更多!他雖然也介紹相同的知識,但卻要在介紹時灌注上一種熱情與推動力。而這種推動力也就是當初驅使他選擇自己主修科目的力量。……事實上,就是他心目中所響往成為的『形像』,使這科目成為他自己的科目。使教師成為教育家的,正是這股促使他有朝一日能成為自己心目中所嚮往的『形像』的驅力,這股力量驅使他朝著一個明顯的目標不斷努力前進。而當初這股推動力之所以產生,難道不是對他所嚮往的那個『形像』的信念而來的麼?目標,教育家和信念融化成為一種「形象」,而這『形像』又領導著人向一個固定明確的方向前進。」
因為蕭滋對「教育家」的瞭解,使他在教學上除了把淵博的學識介紹給學生以外,還特別注重引發學生對所學科目的熱情以及推動學生勤奮學習的那股「驅力」(drive)。這就是為什麼蕭滋眾多的學生,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能在自己主修的科目中全力以赴、執著不移、乃至於出人頭地的原因。學生對蕭滋的愛戴,除了意識到從蕭滋那裏得來的知識,對自己所學科目的熱情,對自己心目中所嚮往的「形象」的肯定,以及向一個明確固定的方向情不自禁地奮力前進以外;還有就是意識到自己在蕭滋生命中的「價值」。蕭滋在同一篇致詞中說:「在評估教師的功績時,經常會把十分重要的『另一半』遺漏掉,那就是學生對教師的價值。試想。每當聽到在面前彈奏的孩子,竟是一位可造的音樂之才;在授課時,眼見一個孩子那麼動奮地練習,那麼殷切地求好,這一切的一切對教師所顯示的意義,不外乎是一種『信賴』!這種驚喜,這種感受,難道不是教師最好的報酬麼?家長把孩子託付給我,孩子又把自己完全地交給我。這種信任,對我來說,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真情。而這種情誼是祇存在於真正的朋友之間的,更何況這種信任又是隨著學生的成長而增加的。」蕭滋的學生不僅肯定自己,也深切地知道他們同時分享了蕭滋本人作為一個「教育家」的生命的價值;這樣,蕭滋的「形象」自然情不自禁地時時出現在他們的心目中。
(五)
一九七○年代的中後期,國內的音樂活動隨著經濟的茁壯而蓬勃興盛,然而,幾乎在每個活動中,都能看到蕭滋的學生,以及他的影響。這種「成就」,對蕭滋而言,或許是「始料未及」的;但是,對台灣樂壇來說,蕭滋的「貢獻」卻是個「奇蹟」!十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四十分,蕭博士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八十有五。他的逝去,固然令生者悲戚,然而,他在台灣所創造的「奇蹟」,亦將隨著中國音樂的歷史而留存在中國人的心中。
|